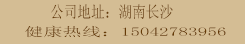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蜈蚣 > 蜈蚣的生活环境 > 本想下乡做一个安安静静的知青,没想到却遇
当前位置: 蜈蚣 > 蜈蚣的生活环境 > 本想下乡做一个安安静静的知青,没想到却遇

![]() 当前位置: 蜈蚣 > 蜈蚣的生活环境 > 本想下乡做一个安安静静的知青,没想到却遇
当前位置: 蜈蚣 > 蜈蚣的生活环境 > 本想下乡做一个安安静静的知青,没想到却遇
第1章:古墓冲
年的春天,我们南阳市魏营中学高二(二)班的同学,几乎都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被分到桐柏县古墓冲生产队的只有我和苏丽两个人。 当天下午公社派老王赶着一架牛车送我们到生产队。走之前公社专管知青的李领导给古墓冲生产队摇了一个电话,可是半天接线员也没能接通。 李领导只好叮嘱老王把我们一定要送到。他说山区地形复杂,悬崖峭壁随处都有,除了注意行路安全之外,千万别让两个孩子迷了路。 李领导表情真挚、态度和蔼,对我们俩十分关心,一点儿也没有趾高气扬的领导架势,这让我和苏丽都是心头一热。坐在牛车上,望着崎岖山路上初春美轮美奂的景色,想家的心情渐渐淡了一些。 赶车的老王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脸上如刀削斧砍的褶皱显出悲苦的神色。我和苏丽私下嘀咕,这不应该是社会主义的表情,怎么看他都像生活在黑暗的万劫不复的旧社会。 快到古墓冲生产队的时候,牛车在狭窄的弯道处发生意外,一只轮子发生倾斜之后突然从车轴套上脱离,颠狂地往前奔出两三米,来了一个相当漂亮的向上跳跃之后,滚下山涧里面去了。 我和苏丽还有老王眼睁睁瞅着调皮的车轮,撒着欢义无反顾地往下冲,无能为力。 终于在山涧的最低处,它气喘吁吁地停下来,左右摇晃几下,倒在光秃秃的碎石间,一动不动了。 老王蹲在山道边,瞧了半天,愁眉苦脸地说:“只有下去,把它弄上来,不然咱们就困在这儿了。”之后,他用期待的眼神望着我。 我非常明白他的意思。一个人的力量不容易把车轮弄上来,老王想让我和他一起下去,好搭把手。 我和老王顺着坡度,攀着凸起的山石,慢慢往山涧里下。还好,我穿着一双老妈花五块钱买的回力鞋,尽管有些大(老妈故意买大的,心细的她考虑到我还在长个子),却非常适合山区行走。 终于下到山涧底部,我刚要伸手去扶起车轮,脚下突然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应声望去,一根长长的黄白色的东西被我无意间踩断了。 “这是什么?”我问老王。老王推着车轮,瞟了一眼,说:“骨头。” “骨头是什么东西?……”我突然醒悟,惊叫着跳起来,落地时又踩在另外一根骨头上。 这时候,我才发现山涧内散落着不少浅黄色的尸骨,藏匿在碎石与浅浅的绿草之内。 “放心,只是些牛马的骨头,过去这条道上经常有马帮托运货物进出,山道又险,发生意外是常有的事儿。”老王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似乎什么事情也激不起他的兴致,包括这些骨头。 我可不这样想,心惊肉跳地四处张望,觉得这里简直是一个露天的坟场。 不远处,一只残缺不全的人骷髅从碎石中半露出来,三只红黑相间的蜈蚣从它黑洞洞的眼眶内爬进爬出。骷髅的眼睛像在咕咕地冒鲜血。 “老……老王,我看到有人骷髅。”我发现自己整个人都在哆嗦。 我不敢停留,随在老王后面往上爬,并且迅速超越了吃力地推着车轮的他。 “骷髅又咋着,全都是些死人,你怕啥。”老王一个人推着轮子,心里溢出不满的情绪。 …… 等我帮着老王把车轮子重新弄上来,并且套到车轴上时,天色已近黄昏。 老王坐在车尾,抠了半天漆黑油腻的指甲缝,这才伸长胳膊,指着前面的山道说:“转过这个弯,下了山,山脚下有两条小路,靠东边是古墓冲,西边是冢头。上面写着路牌的,你们别走错。古墓冲是活人居住的地方,冢头可是个大坟场,而且是禁地,没有人敢去。” “什么意思?老王,你不送我们了?”苏丽问他。 “我得回公社交差,再往前送,回来就得走夜路。我可不想掉下山涧去当孤魂野鬼,再说,一到天黑,这条道上不干净。” “不干净是什么意思?”苏丽满脸的疑惑。 老王终于露出一个鲜活的表情,挤着眼睛故作神秘地说:“没有人敢在通往古墓冲生产队的山路上走夜路——天一黑,鬼要出来,它们乱糟糟地挤在道上。咱们人根本就没地方走,也找不到路可走。” 苏丽一脸的不相信,她有些轻蔑地瞅着老王,说:“你就吓唬三岁小孩吧,我们可是无神论者。你走你的,我们自己去古墓冲就是了。偷懒的家伙。” 我对老王的话将信将疑。从山涧里爬上来之后,我没有跟苏丽透露谷底里那些人和动物的骨骸。既然苏丽表了态,我只好无奈地目送着老王在狭窄的山道上神奇地把牛车转了个弯,架着它离去。 临走时,老王嘱咐我和苏丽:“你们一定看清路标,别走错路,不然的话,会在冢头里走迷,再也找不到回来的路。” “走你的吧,别再宣扬你那一套封建迷信。”苏丽简直有些讨厌老王,她背起行李,跟我说,“我们走,反正快到了。” 往前转过弯道,我们开始在山坡上来回蜿蜒曲折下行。天已经渐渐开始黑下来,几经曲直,我和苏丽终于到了山脚下。 穿过一座青石板铺成的小桥,对面果然如老王所说,有两条岔道。在岔道口的一棵杨树上,隐约看见挂着一块上面写着古墓冲的路标指示牌。由于时间长了,它发生松动,耷拉下来,标示指向地面。 这让我们非常意外。山路绕来绕去,我们早已经不辨东西。路标指示不清,怕是我们也不知道该走哪边的小道。在四周寻找了半天,眼尖的苏丽才发现冢头的指示牌。原来因年代久远,它掉在树下面,已经碎为几块。 天已经彻底黑下来,不能指望看太阳辨别方向。偏偏天气也不太好,无法看到天上的星星来辨别方位。 我和苏丽面面相觑,哪条道是通往古墓冲生产大队的? 四面起伏的山峦,如怪兽般耸立,我和苏丽像两个可怜巴巴任人宰割的小猎物,惶恐不安地徘徊在它们的包围中。没有一个人出现,没有一个人可以企求帮助。 犹豫半天,我们统一认识,右侧就是东,我们应该顺着这条道走下去。就是走错也没有关系,大不了拐回来,重新走另一条小路。 我走在前面,苏丽跟在身后。道上碎石缝里杂草丛生,荆棘密布,荒凉得令人心生恐惧。我越来越怀疑走错了路。隐约间有一只苍白的大手从幽深的荒道里伸出来,轻轻地向我们摆着,招引着我们。 突然,我觉得那只苍白的大手好像揪紧了我的解放绿,我有些身不由己,被拽着磕磕绊绊往前走。苏丽一声不敢吭,在后面紧紧跟着。 渐渐地,起了雾,并且越来越大。四周笼罩在浓雾中,愈发分不清我们身处何方。 碎石咬破了我的鞋底,刺痛了我的脚;荆棘划烂了我的衣衫,割伤了我的身体。可我和苏丽像中魔了一样走在这条杳无人烟的小道上。 浓雾中,不知从哪儿跑出几只受惊的花面红尾狐狸,它们往前逃了几步,停下来,蹲在道边,扭脸颇具戒心地盯着我们。 它们哪里晓得,它们的突然出现也让我和苏丽受到惊吓。 远处的山林里,隐隐狼的一声嚎叫,凄凉中透出悲苦的声音。花面红尾狐狸听得也不禁打了几个颤栗。我有种不祥的感觉,不能再往前了,得拐回去。可当我扭头时,发现后面的路已经看不到了,浓雾中,漆黑一片。 黑暗里涌出一股凉风,掠过我的脖子,刀片一样。我觉得一阵寒意,打了个冷战。 前面的路还依稀可辨,那几只花面狐狸却突然不见了。四周静得我都能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脚踩着碎石和杂草的声音显得很响,几乎听到它们撞到遥远的山峰的回声。不,那不是回声,我怀疑其实暗处有个什么东西一直在跟着我们,如影随形的。我仿佛已经听到它的走动声,还有那故意压抑的呼吸。 但我看不到它,任何想试着去寻找去发现的念头,都是不现实的危险的愚蠢的。刚才像刀子一样的风就是警告,我又怎么能意会不到呢。我闻到了风里的味道,清冷,腐朽,久远,还迷漫着烟尘,决不会是人的味道。 我想,我们必须往前走,没有退路。 我们在越来越浓的雾气中又走了几步,就在红尾狐消失的地方,局促的山道,突然开阔起来。
第2章:隐形
雾在没有一点儿征兆的情况下,突然一散而尽。 古墓冲生产队,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我和苏丽眼前。 一个举着气灯的青年人站在那儿,旁边还立着一个比他大一点儿的男人。 这两个人在哪儿见过?我的脑子里蓦然涌出一种似曾相识的错觉。而且我隐隐觉得能记起他们的名字。他们叫什么呢?我努力想着。一时又想不起来。 站在那儿的中年男人望着我们,问:“是公社来的知青吧?” 苏丽怔怔地望着眼前蓦然出现的村庄,一时间有些适应不了。听到中年男人问话,这才回过味儿来,她迟疑一下,随着我点点头。 中年男人大步迎上来,热情地说:“我是队长楚长生,他是队里会计李明。” 长生队长指着颇具造型感的举灯人。 他们应该叫这个名字吧,我模糊地猜想着,由长生和李明两人带着,和苏丽晕头晕脑往生产队里面走,深一脚浅一脚的,如坠梦里。 我们被安排到大队部暂住。长生队长答应,等他做通乡亲们的工作之后,如果我们愿意,就住到老乡家里去。 大队部坐落在古墓冲生产队中间偏北一点儿,是一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两进灰瓦青砖的大宅院。李明手里的气灯非常耀眼,我能看到院外边有一个近三十平方的空场,空场的东南方有一棵古楸树,上面挂着半只已经考据不出来曾经在哪用过的铸铁车轮子。经询问,我们得知这是古墓冲大队生产劳动作息用的钟。 后来我发现此破铁车轮质地优良,声音浑厚响亮,余音袅袅,颇有古朴之风。只是长生队长不太在乎音律之美,早上上工时当当一通猛敲,下工时又敲得有气无力,显得非常没有章法,白白浪费了这只废物利用的破车轮子。 苏丽恨不得冲上前去,言传身教,教长生队长如何把钟敲好。我有时候也有这样的冲动。真的。当然,仅仅是冲动,不是行动。做人一定要低调,而不是炫耀。 前院东边两大间是大队部会议室,有一小间是播音室。播音室外边种着一棵碗口大的枣树,上面架着一只随时能播报最高指示和喜报的大喇叭。 西边有两间堆放着一些文艺表演的道具,从古代的刀枪剑戟,到抗战时期日本人用的三八大盖枪和李向阳用过的常常代表正义的驳壳枪,此枪俗称二十响。比较离谱的是,在道具里面,竟然还有一尊像模像样的六零小炮。当然是木头做的,乡下的能工巧匠把它做得已经可以以假乱真了。 我一时还猜不透,它能在哪出革命历史正剧里派上用场。 西边另外一小间房子正中放着一面直径足有15米的大鼓,墙上挂着几件破烂的血衣,透过窗户我第一眼看到时,吓了一大跳。长生笑着解释说那是文艺演出时用的服装,不是真的。 没想到这个仅两百多人的生产大队,竟然还有这么齐全的演出道具。长生面露得意之色,说:“我们有自己组织的别样红贫下中农文艺宣传队,县上《桐柏英雄》里唱小花的汉剧名角何飞飞还亲自指导过呢。” 前院北屋中间是进入后院的通道,通道上部呈半圆穹形,看上去有些不舒服。至于不舒服在哪儿,我也说不上来。通道的左右两侧各有一间房子,门却朝北开在后院里。 进入后院东北侧是一处厕所。依次往南,一间堆放着生产队牛吃的麦秸,另一间存放牛吃的细粮碗豆和棉油渣饼。正北屋三间,空着,已经被收拾干净,暂时作为我们的住处。西屋的三间堆放着原来主人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听说此宅院的原来主人在旧社会是地主,解放后畏罪自杀。房子被荒废几年之后,赶上吃食堂饭,就变成了生产队的食堂。食堂解散后,就成了大队部。 南边正中通道,连接前院。通道两侧各一间房。房间屋门紧闭,也看不清楚里面放的东西。长生队长也没有介绍,显得有一点点神秘。 长生带我们参观完院落之后,帮着把行李放进屋里。后院北屋三间,中间是正屋,我住东头,苏丽住西头。东西房都有木门,与相对古朴做工细致的房间风格比起来,这两扇门显然是后来才装上的,粗糙而且是白茬没有上漆。 苏丽伸手一推西屋的门,门吱呀一声,闪出一道缝隙。苏丽突然哆嗦一下,跟着惊叫起来:“谁在那儿?” 长生也吓了一跳,蹿过去一把推开木门。房间内除了东北角放着一张床,旁边用青砖支起一块木板做成的桌子之外,空无一物。苏丽惊魂未定,依然愣在那里,喃喃自语:“我明明看到有个老太太的身影闪了一下,她还扭头看我一眼。” 长生微微一怔,马上又恢复笑脸,搓着手,说:“这里早为你们收拾干净了,不会有不干不净的东西。” 我不放心,在房间里面转了一圈,什么也没有发现。大家都是唯物主义者,不信鬼神信马列。我安慰苏丽:“真的什么也没有,是不是坐车时间长,又走了这么久的路,太疲劳了?” 说着我把她的行李搬进来,放在床上。苏丽小声央求要和我换房间,我当然没有意见,长生却面露难色。 “是这样的,我们这里有个风俗,如果大家都是一样的辈分,男人一定要住在东边,女人住西头。” 他话一出,我和苏丽差点都笑出声,都什么年月了,还信这个。长生愁眉苦脸地说:“没办法,虽说新社会,有些顽固的旧习还是改不掉。苏同志您就入乡随俗吧。” 长生把我们安置好,留下一把大门钥匙就匆匆离去。临走时他说:“其实晚上你们锁不锁大门都行,我们这里很安全,民风淳朴路不拾遗。” 我和苏丽送他们刚出院,李明又拐了回来。他笑着解释说得把汽灯拿走,我们屋里有煤油灯可用。 李明是古墓冲大队唯一高小毕业的人,在这里俨然是一位拥有最高学识有着很高威信的汉子,掌管着全生产队的财政大权。如果他们真的很有钱的话。 他把汽灯熄灭后,整个后院突然就暗了下来。在汽灯熄灭的一瞬间,我突然察觉到李明的目光显得游移不定。 他问:“你们真住这儿了?队长当初收拾那房子时,我就建议让你们直接住老乡家里。” 李明似乎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黑暗中我也能看到他有些慌乱的神色。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情绪,他急忙低下头。 “你的话啥意思?”苏丽也发觉李明不自然的表情。 李明没有回答,提着汽灯往前院走,走出好远,他才扭头说:“以后你就会明白了,不过现在是新社会,我们不会相信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是吧。” “他的话到底什么意思。”苏丽盯着我问。我也听得莫名其妙,一头雾水,只好冲她摇摇头。 大队部只剩下我和苏丽两个人。院落里格外的安宁,远处,不知从哪儿传来耕牛超重低音的叫声,清晰到震撼。刹那间,大队部寥落得有些瘆人了。 突然,我们身后传来一声轻微的咳喘,我和苏丽不由得转身望去。一股细细的凉风从我们身边吹过,仿佛一个看不见的活物慢慢地移了过来。它在离我们仅仅一步之遥的地方停下来,盯着我们。 我和苏丽看不到,但能感知到它的存在。 好在它给人的感觉是温和的,善良的,谨小慎微的。它打量我们的目光充满了征询、疑惑与不安。 “你是谁?”苏丽躲到我身后,冲着那团只存在于我们彼此意识里的隐形物问。 它没有回答,站了片刻,细细的气流袭过我们的衣衫。它从我们身边慢慢闪了过去,往前院走去,只剩下惊魂未定的我和苏丽呆立在后院里面。 “受不了了,我不要住这里。”苏丽失控地尖叫起来,“我要找队长,我要住到乡亲们家去。” 我只好安慰苏丽,说刚才只是一阵风,是我们大惊小怪了。初来乍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精神上有些起伏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知识青年,怎么会相信那些荒诞不经的鬼神邪说和所谓的神秘主义呢? 经过我这样一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苏丽也觉得自己太大惊小怪了。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问我:“你确定刚才的只是一阵风?” 我点点头,很肯定地点点头。 一时之间,我也让自己说服了,并且相信那仅仅是一阵风。 我俩彼此嘲笑对方有些神经过敏,心情就放松下来,这才想起来自己床铺还没有整理,于是进到屋内拾掇自己的房间,把从家里带来的生活用具摆放出来。 我刚把自己的一个包袱打开,苏丽满脸迷惑地拿着一把红布条捆着的树枝走了进来,好奇地问我:“这是什么?” 我接过来,看了看。因为在学校时上过劳动技能课,加上我们经常到郊区的农田果园实习,我一眼就辨认出来它们是桃树的枝条。尽管没有叶子,枝条还是发着新鲜的清灰色,用手一掐渗出汁液,应该从树上折下来没多久。 “桃枝。你从哪儿找到的?”我问她。 她说铺床时,从床上铺的稻草下发现的。 “我知道是桃枝,它们用红布带绑着,放在那儿是什么意思?”她问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知道这东西放在那儿,肯定是避邪用的,只是苏丽不明白罢了。 这些东西当然不能跟苏丽讲清楚。我只是一味安慰她,说这东西没有什么意思,可能是在铺稻草时无意间掺杂在里面的。 她半信半疑,犹豫片刻,随手把桃枝丢在我房间的墙角处。 “我才不要这些破树枝。”她说完回了自己的房间。 苏丽走后我赶紧翻了翻自己的床铺,并没有发现特意放着的桃枝,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但当我望着苏丽丢下的那把红布条拴着的桃枝,心里还是蓦然涌出一股不祥的预感。
转载请注明:http://www.wugonga.com/amly/107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