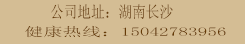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姓王,因为他曾经被划分为“中农”,就称他为王中农吧。
在讲他的故事前,有必要讲讲他父亲,姑且称为老王。
老王出身于地主家庭。他家是我们镇(现在有一部分地区划到别的镇了)四大家族之一,巅峰时期有近三千亩稻田,山林面积也极大。
他属于典型的郁郁不得志之人。十八岁不到就考上了秀才——在我们那小地方,是被誉为天才的。我不知道以前考秀才有多大难度,但从讲述人的语气来看,是不啻于现在的人考上“清华”“北大”了。并且,他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曾北上武昌求学好几年。可是,他的父亲,一个古板的地主,强迫他回家娶亲生子——他家已经是三代单传了。
可能是由于理想的幻灭吧,他于是用极端的方式折磨自己。成亲后,把平时读的书和纸墨笔砚一把火烧了,发誓再也不读书,似乎把写字也戒了,过年的对联,自己都不会动手(能考上秀才,字应该差不到哪去)。
可能小地方确实没有人能和他交流,因而,他变得很沉默,极少出门,遇到熟人,顶多点头示意一下,绝不会停下来聊天。在家,也不和家人同桌吃饭,都是下人另烧一份送到他房间,逢年过节也是如此。
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收集药方(草药居多,很多都是口口相传,没有文字记载的),所以,能和他说上话的,都是一些土郎中或有药草秘方的人。对此,他似乎到了痴迷的境界。
有一次,他听说有个人知道治蜈蚣咬伤立刻见效的药(被蜈蚣咬,没有什么大危险,但极痛,忍忍就过去了,药方其实也属于鸡肋),居然用三亩稻田去换。可以说,他是一个草药偏方的集大成者(我们那)。
但是,他又从来不给别人看病,有人求他,他就会告诉那人:“你到某某(会治这病的人)那去,他会治”。他开辟了一大块地用来种药,叫人用很长的竹枝围得严严实实,平常是不准别人进去的。据说有一次他老婆看里面的花开得很好看,就叫丫鬟去摘了一把,他居然大发雷霆——他涵养很高,所谓雷霆,也就是瞪了眼不说话。不过,有人病了,某郎中说你到老王那里谋(要)点某某药,他又会毫不吝惜,一挥手,你认得就去扯——反正他不会动手。他日常的工作,要么在药园里伺候药草,要么扛了锄头到山上挖药移植到园中。
他也不喜欢经营什么,从来不买田地。自家的地,让谁种,收多少租,他一概不管,都是一个管事的先生说了算。遇到年成不好,有人交不了租,也只是年前派人到那人家里对个账,从不通牒什么时候必须交——我们那算是自给自足的地方,歉收的时候少,而且以前的人思想淳朴,最怕欠账了。
因为这样,他在人眼中,也就是一个怪人了。后来年纪大了,性格才变得随和了一些。我想,他是寂寞得太久了,或者是认命了才这样,因为他后来对风水产生了兴趣。
在我看来,中国人,不论高低贵贱,灵魂深处,似乎都有一种大兴土木的情结。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地方植被破坏是很严重的。所以有”蜀山兀,阿房出“的诗句。老王那个时期,我们那靠近县城的周边地区,建房用的木材就已经开始稀缺了,于是,没钱的人家,就只能去偷了。以前我们那到县城的交通还算方便,所以进山偷木材的人比较多。村里人那些没事的年轻人,往往会组织起来扛了土铳护林。
一天晚上,一群偷木材的人大概是迷了路,居然摸到离村庄不远的地方砍起树来。晚上声音传得远,被人听到了。这些护林的青年,各个很兴奋——要是离村远,打起来说不定会吃亏,现在靠村这么近,绝对不怕打不过。
于是用了围捕野猪的方法,悄悄把这些偷木材的人包围起来,先朝天放了几铳,然后大喊:“捉贼啊!捉贼啊!”那些偷木材的,吓得到处乱窜,纷纷没命逃跑。这些护林的青年,计划得很好,但最终一个偷木材的都没抓到,心里很不服气。
忽然,听到林中有窸窸窣窣的声音,追上去一看,是两个人,一个十六七岁,一个十四五的样子——年纪小,吓得找不到路了。于是护林的这些人用土铳逼两个人把刀扔了,然后冲上去拳打脚踢,直打到两个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才停手,然后扯了两根捆柴的葛藤死死捆了,像抬野猪一样抬下山。
因为这山是老王家的,于是他们就把两人抬到老王院子里一扔,大叫(这时老王一家早已睡了):“老王,老王!捉到两个贼,偷你家的木(木材)”老王一家上上下下都纷纷起来。
老王老婆一看这情形,连声说:“造孽啊!造孽啊!你们把人打成这样做什么?”连忙叫人把两个人松了绑,叫大家到大厅里去,然后吩咐丫鬟去做饭。
老王后起来,一看这情形,直摇头:“你们这些后生,真不懂事,这是两个小孩,毛都没长齐,把人家打成这样!”
护林里面有个后生听了,大声嚷起来:“小孩就偷东西,还打不得?今天是偷你家的,要是偷我家的,我要把他打死!”
老王只是笑笑,说:“你这么厉害,等一下不喝半坛酒不准回去!”
两个小孩这时已经吓得浑身发抖,站都站不起,只能躺在地上。老王于是叫“长年”掌灯,到药园中扯了草药榨出汁水,对两个小孩说:“喝了!”两个小孩以为是要毒死他们,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老王叫他老婆过来说:“你快要他们喝了,这两个都伤了内脏,迟了以后治都治不好!”
说完,回头对护林的后生说:“你们要吃什么自己到灶前(厨房)去说,我精神没你们好,要睡觉!”然后头也不回就走了。
老王老婆这才告诉两个小孩,这是“贼牯药”,什么叫“贼牯药”呢?按我们那说法,就是不管伤得多重,只要刚受伤喝下去,能保住内脏,不会落下病根。因为最初是做贼的人防身的秘方——做贼必定会失手,失手肯定要被打,吃了这药,能保命。
那边,偷木材的同伴纷纷回到了家,一点人数,发现少了两个人。开始还相互安慰说肯定是小孩走得慢,可快天亮了,还不见人回来,顿时都慌了神。两个孩子的母亲,听说他们被追的时候到处有土铳声,害怕自己的儿子已经被打死了,双双急得晕死过去了。
我不大清楚以前对打死正在实施盗窃的人会怎么判决,印象当中,似乎死了就白死。因为解放前,我们那就活生生烧死过两个外地流窜来的小偷(人性中野蛮的一面似乎永远不会消逝),所以,这两位母亲的担忧是合理的。
他们这个村也是一个大家族聚居地,于是,族里说得上话的,把人组织起来商量怎么办。大家的意见是:先派一个人去探探情况,到底是打死了,还是扣住了,然后再做决定。为什么只派一个人呢?因为错的是他们这一方,人去多了,会让别人觉得你想仗势压人,稍有言语上的不妥,很容易激起宗族斗争——农耕时期,宗族的荣誉是很重要的。
难题是到底派谁去呢?这绝对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弄不好,还会挨打。大家都不大敢。
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说:“那就我去一趟!”话一说出口,大家就直摇头,这个人姓彭(这家族都姓彭),五十开外,平时话极少,从不和别人争论什么,属于木讷型的人。
族长担心他不会说话,把事情闹大,就委婉地说:“这个,要能把事说圆(大概意思是说要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老彭(这么称呼了)说:“两个小孩不懂事,砍两根木头,没多大事,我去一趟。”因为没人,族长只得同意了。
老彭一到我们村,找了个人问:“老表,我屋里(含有家族的意思)有两个没用的,昨日到你们这来砍木,你晓得在哪个地方么?”
那人回答说:“两个小孩吧,在老王屋里(农村小道消息传播极快)!”然后指了路。
老彭见到老王,还没开口,老王倒先说话了:“你是来接两个小孩的吧?我还准备让他们吃了中饭再回去!”
老彭说:“是啊!真是没脸没皮,实在对不住!”
然后把两个小孩家中的情况细细说了一遍,终究是穷苦。之所以会来偷木材,是因为想积攒木头,以后好建房——他们家的房子快倒了,父亲又都过世了。另外,在农村,房子不好,是没有女子愿意嫁过去的。
还没等他说完,老王就说:“没事,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哪家没有个落难的时候?只要是自己屋里用,你过来跟我打个招呼就是,这木烂在山里还不就烂了。就是而今有些人心太大了,砍了去卖,这是要不得的!”
老彭连忙保证:“老兄你放一万个心,日后我们那还有人过来砍木,你找我就是!”
老王笑笑说:“这两个伢哩(小孩)屋里急得不得了了吧!这样,我就不留你了,既然劳你来了,就到我这扛一根干木(风干的木头)回去,这两个伢哩昨日吓到了,肯定扛不动,我喊人帮他们扛了送到某某地方!”
老彭连忙说这怎么好意思,老王一挥手:“几根木值不了什么,就是你回去跟他们屋里(家长)说说,这么小的伢哩,要珍贵一下,昨日夜里,我们这的后生要是发猛(耍狠),真的用铳来打就真没命了!”说完,就吩咐两个长年带老彭及两个小孩到牛栏楼上挑木头(农村木头一般放在牛栏上面)。自己就进屋了。
老王有个特点,说话但凡挥了手,就是送客的意思,不会再说了。选好木头,老彭吩咐两个侄儿领了“长年”先走,说自己还要吃筒烟。
老彭独自在老王房子周围转了转,然后掏出烟丝,对着屋里喊:“老兄,出来吃筒烟哦!”
老王有点纳闷,但还是叫丫鬟搬椅子出来晒太阳(这时是秋天),两人就默默地叭着烟。
许久,老彭发话了:“老兄,我看你这屋做得不久啊(刚做不久)!”
“也有十几年了!”老王说。
“你屋里在这住了蛮多代了吧?”老彭问。
“从老公公(曾祖父)开始就住这里。”老王说。
“我看你屋里钱是有蛮多,但这屋却不敢多做,只能依你的老宅的地盘(地基和方位)”
老王一听,大吃一惊,因为这是他家族的秘密,祖上有交代,不管有多发达,房子的格局不能变。这件事,只有老王知道,对他老婆都没有说。
但他嘴上还是轻描淡写地说:“这有什么说法呢?”
“怎么说法?老兄,我这个人从来不多说话,都是别人说我听。刚才听我两个侄子讲(按辈分,那两小孩应该叫他叫叔叔),不是你,他们可能命都没了,今我就要多两句口,你莫见怪!你这屋,一般人不敢在这建,肯定有人点化过!”
老王顿时大惊失色。他曾祖父当年很穷,他家以前在我们那又属于杂姓,老宅被大姓兄弟堵得没了出路(其实是变相霸占地基了),没地方落脚,只能搬到这个地方(相对来说很偏僻)。为什么选这呢?因为他曾祖父当年放牛没事,喜欢和经常到我们那要饭的一个落食子聊天。
这一年,这落食子看到他家房子被堵死,就对他说:“后生,我帮你指个地方,保你几代富贵,就是人丁不盛,你要不要?”一听到“富贵”,谁不动心呢?至于人丁盛不盛,只要不绝代就行了。
当年划地基的时候,这个落食子就说:“后生,你这屋要做大点,日后佣人丫鬟还要住!”
据说,这个落食子还在这房子大厅放祖宗排位地方的地下,埋了一些神秘的东西。等着房子做起来,他家就顺风顺水,养母猪,一窝生十几个,连母牛都双生过,家中的财富逐渐积累起来,经过三代,才到现在的规模。这个,外人绝对不知道。
老王于是对老彭刮目相看,说:“老兄,还是到屋里去喝口茶水吧?”
老彭笑笑,说:“茶就不喝了,就在这吃筒烟就走!”
老王又问:“你说我这屋是有人点化了,这个怎么说呢?”
老彭顿了顿说:“我说了你莫生气,你这屋,要做得非常准,稍微偏一下,莫说有你这家产,一代就会住绝(人死光),你这是块邪地,你看!”
然后指着房子及周围的地方还有远处山峰说:“你这是个灯盏地(外形像灯盏),这房子要没做准,再大家产都要烧光。做准了,正好可以照着保你!你厅里,肯定埋了东西,不然,肯定镇不住。”
“那当年人家说这地方只能保几代,你看是这样的么?”老王问。
“呵呵!”老彭笑笑不语。
“你直说,不要紧!”老王说。
老彭犹豫了一会,说:“老兄,你这屋,已经住不得了,再住,香火要断!”
老王说:“这样,那看来要搬,你看这附近有好一点的地方么?”
老彭说:“搬啊,别人搬可以改一下运道,你屋里不行,搬也没用!”
“这又是怎么个说法?”老王问。
“你这屋,盛起来,靠的是一股邪气。当年帮你家看风水的,有大道艺(本领),这地方的邪气出来,靠的就是一个眼,那个师傅把这眼堵在你屋下面,他们出不来,只有护佑你家盛,等你家里气数用完了,他们好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你家盛得这么快!你要陡然(突然)一搬,没人镇一下,会更啰嗦(方言,麻烦的意思)!”
老王顿时落寞起来,这时,他自己也懂些风水,但只能看到“形”,看不到“气”,虽然有预感家族可能要败,但不知道会败成什么样。老彭这么一说,也大致明白了。
老彭见老王如此,就安慰他说:“老兄,我没什么道艺,依我看,把你门前这路改一下,看能不能化了这一劫!”
“怎么改?”老王问。
老彭起身,指着门口说,当年,你屋里为什么把路修得绕到你家(老王家住在半山腰,山不高)而不直接修上来呢(直线,要省好多路),就是为了主财。而今,你把路改到从你大门口直下到山脚下,破点财,看留不留得住些运道,趟过这一关。”
老王正要再问路要怎么修,老彭却起身告辞:“已经晚了,我要回去,今我也说打乱话(胡说),你莫见怪(责备之意)!”然后扛了木头就走了。
随后,老王做了一个当时大家都不能理解的决定:把自家门前老路废掉,从大门口直修一条新路下到山脚,短短一段距离,居然转了三个弯。
有点风水常识的人都知道,一出大门就是下坡路,是很不吉利的。附近的人都纷纷议论:这老王恐怕是作死(按我们那说法,人接近死亡时,往往会做一些离奇的事情),不知道听谁“嚼蛆”(胡说八道)修这么条路!
当然,后面的事情,证明老王的这一决定,应该说是很明智的,讲他儿子王中农的故事才会体现。
写(复述)这故事,很是纠结,很多细节,其实我也知道,一笔带过,从叙事的角度来说,是更好地。之所以叙述得这么冗长,是因为我觉得,像老王这样有才华学问的人,一生只留下一个玄幻的故事,实在可惜。
他的善良、傲气和乖张,很有名士风范。他的同窗,用他的话来说,学问在他之下的,有的做官,有的纵情得意。只有他,守着几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稻田,老死于穷乡僻壤之中。我们常人,总是感叹自己为贫穷所困,为低贱所困,其实,从老王来看,又有多少人是为富贵所累,为荣华所绊呢?有些官二代、富二代,若能生在平常人家,何尝不是有机会凭自己创出一番功业,最终却只能在父辈庇佑之下,庸庸碌碌。
老王也算老来得子,快四十才有这儿子——前面生了好几个,全都夭折了。
和他父亲不一样,王中农在读书方面似乎没有任何天赋,十几岁的时候,才勉强会“做文章”。一般的父亲,总是希望儿子能完成自己未竟的心愿,而老王对儿子的教育方面却向来不闻不问。
教书先生知道老王的大名,有一次对王中农说:“你拿回去给你爷老子看一下,问问他你做得怎么样。”
王中农兴冲冲回家把自己的作品给他爸欣赏,老王正在栽药,略略看了一下,淡淡说了句:“还做得!”这句话,在我们那方言里,含义比较模棱两可,既可以理解为“不错,很好”,又可以理解为“勉强可以或差强人意”。
因为父亲实在太强大(读书做文章方面),王中农天性之中,对父亲有敬畏之心,所以不敢多问。
老王老婆于是问他:“某某这文章到底做得怎么样?”
老王淡淡回答:“我是十八岁中秀才,他呀,我看到八十岁差不多!”老王不苟言笑,这可能是他这一辈子开的唯一的一个玩笑。
虽然读书不行,但王中农的聪明,是得到大家的认可的。他擅长吹笛子、拉二胡,其他一些我们那的乐器,统称为“家什”(打击乐器,如鼓啊、锣啊、罄之类的)样样精通。
我们那有种戏剧,叫“三角班”——人物只有三种,生、旦、丑,“生”是男主角,“旦”为女主角,“丑”属于插科打诨的,因而叫三角班。没有什么大剧团,都是草台班子,有演出,只要是王中农“打家什”(负责乐器这一块)的,必定是最强大的演员阵容。
另外,王中农人长得高瘦,面目俊秀,皮肤白皙,演旦角扮相极佳,唱功也好,到外村去演出,很多人都不相信他是男的,仰慕他的年轻女子自然非常多。这些演员,可以算得上是发烧友了——没有专业舞台,观众就是地方百姓,没有赞助,全凭一腔热情,唯一的收入,就是微薄的门票收入(由各村筹款),一场下来,也就是导演演员剧务能聚在一起吃一顿较好的饭。
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一方面对表演艺术热情很高,另一方面,对演员这一行业,又极其瞧不起,认为这是很低贱的。像王中农这样的子弟,热衷于演戏,也算是家门不幸。
所以,每次出去演出,他母亲都极力反对,有一次,叫了家中长年,把他按住把鞋脱了藏起来,他就打了赤脚走到剧场——距他家十几里路,而且这时已经是冬天。
另外,王中农在木工这方面天分极高,几乎是无师自通。以前农村碾米,叫“砸米”,是一种用水车带动碾头的自动工具,榨油需要用到碾盘——用水车带动一种类似旋转木马的工具,下面有一个圆形的碾槽。
在农耕文明时代,这几乎代表了木工的最高成就,因为碾头、水车、碾槽以及那类似旋转木马的部件,都需要把直的木头弯出非常大的弧度,然后很多弯出弧度的木头再组装,只要计算稍微出错,一是组装不成,二是容易损坏。
这工作,不是熟练就行,还需要灵感和天分,一般的木匠,终其一生,不敢去试一次(这些部件用料极多而且讲究,稍微出错,所有部件都要报废),王中农也只是在专业木匠工作的时候在旁边看,然后问问,就自己琢磨出来了——核心技术,别人绝不会轻易说出来,这是他们吃饭的本钱。
有一个地方,打算造一台碾坊(兼榨油坊),但苦于木匠师傅没空,王中农知道后,主动揽下这活。大家当然不相信他,因为他连木匠都没学过,于是王中农许诺:没造成不要钱,把材料报废了的话双倍赔偿。大家看他家有钱,就让他去试。他也不请帮手,独自一人在那选料制作了一个冬天。据说,到了安装这一天,全村出动观看——没人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厉害的人物。没想到,他居然成功了。
后来,我们那最有名的木匠(我们周边的碾坊和榨油坊都是出自他或者他徒弟之手)也特意到我们村看王中农造的东西,看完后感叹:“我这手斧要把他扔掉了,我造了一世,水车转得没他造的快(水车质量好坏,就看在同等水量下谁造的转速快)!”
这个碾坊兼榨油坊我小时候见过,工作了几十年没修过,运转状况仍极好,可惜后来被当做废木料贱卖掉了。
像他这样的人,随便学点什么,都足以“傍身”,但他家这么大的家产,学任何手艺,对他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只能做一个无所事事的“公子”了。
世界上很多人,似乎是不能理解的。我们那,喜欢王中农的姑娘不知道有多少(有些是因为他的家境),但他没有丝毫兴趣,年纪轻轻,却喜欢到风花雪月场上厮混。
很多人现在都在感叹世风日下,但我认为,中国在某些方面,其实是没有什么“风”可言的,比如风月场所,恐怕除了新中国成立后那一段时间,真正达到了“圣人之治”的景象,其余时间,应该没什么区别。
以前有一条从我们县到现在的邻市的要道从我们村经过(旧址还在,一米多宽,全部由石板铺就),路旁边,就有很多“妓寮”,为什么叫妓寮呢?因为都是由茅草屋组成,不能称之为楼或屋,只能叫“寮”了。规格肯定不高,据说,那些挑担的挑夫,用两升米(我们那量米的容器,大小不等,但一升顶多有一千克)就能睡一觉,王中农却乐此不疲。
老王对此好像也不大在意,倒是他的母亲,觉得丢尽了脸,经常教训,但效果不大。王中农的母亲家,是我们那靠近县城地方的地主,而且在城中也有很多店铺,产业比老王家还大。
按我们那习俗,家里孩子不听话,终极杀手锏是什么呢,就是他舅舅。一般来讲,叔叔伯伯,是不好动手打侄子的,但舅舅不同,舅舅打了,那是天经地义——结婚,舅舅是上席,他不出现,是不能开席的。
王中农的两个舅舅也是读书人,算是书生。但在老王面前,就矮了几分,根本不敢摆舅舅的架子。于是王中农的母亲等老王出去办事去了的空当,捎信给两个弟弟,叫他们来教育自己的儿子。
读书人嘛,自然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礼了。王中农也不反抗,说什么答什么,两个舅舅觉得外甥也是误入歧途,自己一番教育后,定能浪子回头。等到两个舅舅要回家,王中农极力要求去送。看到儿子这么懂事,做母亲的自然欣慰。
谁知道,傍晚时分,两个弟弟又和儿子回来了,问原因,说是忘了到老王药园中带点某某药回去,就折回来了。
第二天,王中农又在傍晚时分带着两个舅舅回家了,又说忘了去跟某个人说件事。王中农母亲觉得蹊跷,自己两个兄弟办事一向稳中,就算忘了,也只要一个回来就是。于是去打听了一下,一下子气得差点晕了——这两天,王中农带着两个舅舅在各个妓寮寻欢作乐。一怒之下,拿了棍子追着两个弟弟打,并咒骂:“你们两个,就是我死了,都不要你们来奔丧!”
王中农母亲家家教很严厉,王中农是如何成功撺掇两个舅舅到妓寮玩了两天,就不得而知了。但这件事,是我们那的一个大笑话,老年人谈起以前往事,这是必提的。
王中农嗜好赌博。我想,最初发明赌博游戏的人,一定是一个人性艺术的大师,能洞察人灵魂之中的弱点。所以,上至达官贵人,下到贩夫走卒,都有一生沉迷于此的。
对于有钱人来讲,流连风花雪月之地,只是于道德有亏,真正称得上“销金窟”的,还是赌场。
在我看来,赌场(赌局)上几乎就是一个财力炫耀场,只有对等阶级的人,才能聚在一起赌博。
前面我提到过,我们那有名的地主有四家。巧的是,四家之中,都有好赌的“公子”,有的是家族中的儿辈,有的是孙辈。所以,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豪赌”,他们赌得有多大呢?有人一晚上能输掉几十亩地——这在我们那小地方是极其巨大的数字(当然这种情况也少)。
说来也奇怪,按说老王饱读圣贤之书。对儿子这一劣迹,应当是深恶痛绝的。但是,他的态度仍是“不大在意”。只有王中农的母亲,倒是对此经常忧心忡忡。
有一次,王中农输红了眼,私自把十几亩地当做赌注输了。债主上门来写地契,王中农的母亲气得拿了绳子去上吊——封建思想的女性,认为生了这样的儿子,是愧对列祖列宗的。
老王却反应不大,很爽快签字画押。淡淡对王中农说:“我们几十岁了,这些田也带不走,你能改,是最好,改不了,看你怎么到世上做人。人就怕先甜后苦啊!”
另外一个经常和王中农一起赌的人,却没有这么幸运。在一次输掉二十多亩地后,他父亲一怒之下,把他捆起来,然后召集本家辈分高的人召开家族会议。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居然提议“行家法”——把人绑了石头沉到水潭里去——以前有的人家儿子多,也就不怎么珍惜了。
还好这个人的老婆,还算有主张,半夜用斧头把窗子砍开,放了自己的丈夫出来,然后双双逃命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其实,这晚,也有人看守的,只是毕竟是人命,跟自己又没有多大利益关系,因而就装作没听到。每次听到这,我都有点心惊胆战。以前,人性人心却有善良淳朴一面,但野蛮起来,又和野兽无异了。
老王没死之前,王中农还有所顾忌,运气也还好,虽然输了不少钱,但家中根基未动。老王把自家门前的路改道后五六年,他们夫妇就先后去世了。王中农这时已年近三十,却还没娶亲——他的名声实在太坏,对等人家看不上,一般人家,老王家又看不上。
王中农一下成了“孤家寡人”,就更无度了。他的运气也变得很差,年年只能卖地卖山为生了。
有一次,他的运气极好,赢了一大笔钱——那时人用包袱,整整一包袱“现洋”。半夜回家(我们村没人能陪她玩的,都在外面,靠近县城),半路上,看到一个小孩蹲在地上哭,他看小孩哭得伤心,就上去问:“你这三更半夜在外头哭什么?”原来小孩半夜饿得睡不着,打算起来偷番薯吃。
当时正值夏天,番薯才小拇指粗细,又好几天没下雨,地里很硬,根本挖不出来,所以哭起来。小孩见王中农背了包袱,以为里面是吃的,就对王中农说了。
王中农听后,笑了笑说:“我每天背一铺(形容很多)出门,回来都只剩赤膊(输得什么都没有),今天也是你财气好(运气),来!”
说完,解开包袱,抓了两大把现洋叫小孩用衣服包着,说:“明日去买吃的,不要告诉你娘爷(父母)!”说完就回家了。这小孩,他根本不认识(邻村的)。
王中农那两把现洋,在当时,可是一笔大钱(对农民来说),可以买二三十亩地。小孩其实是苦命人,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哥哥过日子,哥哥家小孩也多,一家人每天都吃不饱。
他哥哥一看这么多钱,打算用它建房子。他嫂子虽然只是一个农村妇女,但很深明大义,对他哥哥说:“这是某某(小孩)的,我们不能用,你家几代加起来,斗大的字都人不到一箩(装谷子的容器,容积两三斗吧),就让他去读书吧!”小孩也是争气,一直读到县城去了(学历相当于现在初中,但当时已经很不容易)。
还没等小孩毕业,他嫂子就一病不起,临终前,她托人把小孩叫回来拉着他的手说:“某某,我打听到了,给你现洋的是某某地方某某人,我和你哥哥穷,报不了恩,所以就没去谢他,这个恩,你要记到(记着)!”
那时候(大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未考证)全国到处招兵,小孩毕业后就参了军,而且是红军部队。部队看他有文化,扛枪打仗可惜了,就安排他做军医。解放前,他已经是高级军医了(怎么个高级不大清楚)。
土改时期,他转业到我们市当干部。一回家,就向侄子打听王中农的近况。因为王中农的名声(作为败家子)极大,所以很快就打听清楚了。
这个时候,王中农的地已经被分了,他家的房子虽然大,但比较偏僻,没人愿意住,所以他一个人住了。并且被划分为“地主”——当时,政治环境,划成分好像还没和政治挂钩,都是工作组评议一下,似乎还会征求本人的意见。有一些人,其实也没多少地,但觉得划为“地主”是一种荣耀,故意把自己的田地面积夸大。
对于以后的政治风暴,很多人其实已经预测到了,这位干部就是其中一位。
他以探亲为名,回到家中,然后找“联队”干部问:“某某现在是什么成分?”
联队干部想都不用想,回答说:“是地主成分”,干部也没有做声,先回到他侄子家。半夜,和侄子偷偷来到王中农家。
王中农此时已经灰头土脸,一看干部模样的人出现,心里有些虚了。干部笑着自我介绍:“老王,你怕不认得我了吧?还记得那年你抓了两把现洋给一个小孩吗?我就是那个人啊!”
王中农这才隐约记起来。两人寒暄了几句后,干部问他:“解放的时候,你到底还有几多田几多山?”
王中农因为吃喝嫖赌,把大部分家产耗光,土改分田地的时候,只剩下三百多亩地,山林面积还挺大,茶林所产能榨六七十“榨”油(一“榨”大概四五十斤油)——他虽然好赌,但人很聪明,也不是全没底线的。
干部沉吟了一会,说:“这样就不好办了,那些地都有地契么?”
“画我爷老子名的,差不多都卖了,这三百多亩,画的是我外公的名。”
“怎么会画你外公的名呢?”干部问。
这中间,又有一段故事。天下父母都一样,女儿出嫁,总怕她在婆家受委屈。王中农母亲是他父亲唯一的女儿,所以特别受宠爱。出嫁前,父亲特意花高价,在我们村买了三百多亩田作为嫁妆。之所以签他自己的名字,是想女儿在婆家能有底气——你家几百亩田都是我带过来的。
本来,这地契等王中农母亲嫁过来就要换,但两家都是大户人家,也没太在意。王中农和他父亲关系不是很融洽,对母亲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一直不忍心卖掉。于是,他把其中原委,对干部细细说了。
干部一听,显得非常高兴,说:“这样,这事情就能转成(想办法弄好的意思)!后天我还会到你们联队来,你早点到队里(村委会性质)去闹,说你成分划高了,不要怕,闹的越凶越好!”然后又交代他要怎么怎么说,王中农听完后点头答应。
第三天,老王一大早就到村委会门口。此时他虽然落魄,但还有一股傲气,也有点贵族(似乎不恰当)的矜持,自然不屑和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村干部吵,只是挑了一个干净的地方坐着,也不说话。
那干部怕王中农没那么早,特意迟了一些到我们那“检查工作”。一看到王中农坐在那打瞌睡,故意高声问:“老乡,你蹲在这有什么事么?”
王中农这才如梦初醒,大声说:“我成分划高了,要来改!”
村干部没想到会出这乱子,连忙大声呵斥:“你还高,没把你划作地主恶霸拉去打靶就算好了!”
干部连忙说:“群众有问题,我们还是要有耐心,凡事实事求是,这样,今我就先解决一下你这问题,有事到里面说。”说完示意王中农进屋。
干部在大厅正中间位置坐定,就问:“老乡,你说你成分划高了,你而今什么成分?”
“他们划我是地主,我又没什么田,就是茶山有两块(两在方言中是概数,表示比较多的意思)!”王中农说。
“你少嚼蛆,而今村里还有你家的地契,这你还翻得了案?”联队书记愤怒地说。
“那是我外公家的(他两个舅舅,一个死了,一个逃到台湾去了),地契上画的是他的名字,你们可以拿出来翻一下。”
“这怎么回事?”干部问。
村书记不明其中原因,以为王中农想耍无赖让自己下不了台,火气一下子上来了,狠狠地说:“某某,你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村里哪个不晓得这是你娘老子的嫁妆?这几十年的田租都给狗吃了?”
王中农一下子没了主意,还好,干部立马接话:“这个不要吵,凡事实事求是就好!”然后指了一个干部说,你去把抄(抄家)过来的地契找出来。
没多久,就全找来了。干部故意慢慢地看,看完,一字一顿说:“按地契来看,这田是不能算到这个老乡身上,至于租是谁收了,要两边来对质(老王把他外公家的情况跟干部说了),两家人的事,外人也说不清。依我的意见,是要改一下。”
村书记也是一个没眼力见的人,一心要把王中农地主身份坐实,连忙说:“不算田,他家的山那么大(面积),也够地主!”
干部听了,笑笑说:“几块山就算地主,你们是没出去过,我们这是小地方,你晓得真正地主什么样?那排场——吓死人!”
在一旁的村长,人很精明,一下子理解了干部的意思,连忙说:“是啊,是啊!我们这山里人,谁没点山!”
书记这才明白过来,赶紧补救:“是啊,我是个泥腿子,没什么见识,以前也不晓得转弯(变通)。”
于是干部一拍板:“那这样,你村里开张证明,正好我要回去,顺便把这事办了!”
干部这一拍板,把王中农的成分降到了“中农”。当时,这好像没多大作用,但后来运动不断,王中农能保命(至少是没受苦),全靠它了——我们那“斗地主”运动搞得很大,持续时间也长,王中农手无缚鸡之力,性格又高傲,生活习惯也不好,真要划为“地主”,不死,也要脱十层皮。
最有意思的是,王中农以前一直不肯结婚(有点类似现在单身贵族),落魄后,反而在这方面有心思了。他人生得秀气,又能拉会吹(笛子)还会唱戏,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居然奋不顾身嫁给了他(王中农此时年近五旬,这女子也算是大叔控了,在当时,这也称得上奇闻了)。并且,还一连生了三个儿子。
听说,农村最苦的时期,就是“大公社”的时候。所有人要每天按时出工。王中农什么农活都不会,连最基本的放牛都弄不好。对于这样的人,谁也没办法,只好安排他修理碾坊和榨油坊,所以,他几乎每天都泡在其中。
有社员反映他偷懒,他只淡淡说一句:“你有这道艺,我就跟你换一下!”此话一出,别人自然无话可说了。
改革开放后,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但他老婆很精明,在我们那开起了小店,算是第一批富起来的家庭了。他名义上是每天看店,但其实什么都不做,也许是什么都做不了。他对钱财好像没什么概念,有时候他老婆有事,别人来买东西,他称也不称,随便拿一把给别人。所以,一般他老婆是禁止他卖东西的。
后来,赌博之风又在农村兴起,有人问王中农:“老王,你是这方面老手,怎么不去摸几下!”王中农不屑地说:“这像捉虱子,一天能抓多少!”这话,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霸气”啊!
据说,当年老王改路的时候之所以把路修成三道弯,其实就暗示了王中农人生三次转机——一是输钱卖地,二是送小孩钱,三是干部报恩。只要有一步转机没抓住,他家这香火就要断。当然,这也许有附会之说,但为什么转三道弯,确实奇怪,肯定有些特定的寓意在其中吧。
转载请注明:http://www.wugonga.com/amly/109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