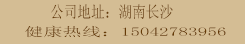编者按:作家朱琺现居上海,除写作外还是一名高校教师。《飞象》出自他的小说集《安南想象》、根据另一部小说集《安南恠谭》中的《安南阿Q做皇帝,还有史前飞行器》缩写而成。《安南齐天大圣之未遂一个名叫强暴的大王》也出自《安南恠谭》。朱琺为自己撰写的简介如下——我保留了其巫师帽状的格式——
朱琺简介
小说家高校教师悖论爱好者越南古籍达人自封前西湖湖长形式主义狂热分子妖怪向博物学发烧友博卡(文学)青年队副队长致力于中华杜撰学、中华附会学、中华影射学『另名:马达+S+狐猴、子不语鸟兽鱼虫』
安南故事
(选两篇)
作者:朱琺
飞象
(选自《安南想象》)
「飞象!飞象!」
如果这个句子在你的耳畔响起,你率先能想象到的,想必是一秤热闹的棋盘上空,一个粗豪而直率的声腔。楚河汉界,车马炮对将相和士。这种红与黑的战争不见硝烟,却现出紧张的气氛;旗鼓相当,界河两边默默对峙着遥相对应的棋子,用异体汉字标志出你死我活、不降不走的不同阵营:当——
红方隔空用「炮」,黑方架「砲」飞射;
红方「傌」壮人强,黑方「馬」蹄轻疾;
红「俥」杀伐果决,黑「車」纵横开阖;
红架「仕」于九宫,黑军帐里上「士」;
还有红「兵」黑「卒」、红「帥」黑「將」——但根据我的看法,这里的「卒」得念bīnɡ(在渡河之际,若是把「兵」也念成zú,问题似乎也不大),而「帥」则读jiānɡ。若是你不同意帅读若将,我还可以举出一个证据:当黑方的车马炮或小卒(bīnɡ)对着红帅照将即将军之先,棋手高高地把个精致圆润的玉棋子拎起来,配上啪的声音,铿然落在纹路细腻的石棋盘上,再在口中悠然或者断然、沛然、猛然喝出一个「将」字来,如若那红帅真读作shuài,那只能叫作文不对题、一知半解,还有就是突出奇兵:一声「帅啊」;甚或仿「将」有去声和阴平两读法,贼兮兮地溜出一句「shuāi(读若衰,或者摔)啊」,很可能会引得对方棋手思路中断,抬起头来一脸茫然「唔,什么?」甚或心浮气躁勃然作色借题耍泼「你才衰呢」「你倒是摔啊?」之类——不信者请试试——但至少,现在的象棋还不曾这么混淆视听,可谓之攻心战术。
现在,象棋棋盘上还剩有一对异体字,就是黑「象」与红「相」。从这种棋叫「象棋」而不是「相棋」,可知士相相辅之说只是皮相,而「象」才是正字。我曾经在《安南怪谭》一书中一篇叫《象棋的故事和借尸还魂》的小说中提到,世界上真有过「象」棋。那是在交趾历史上,曾经有一次,真的把大象当成了棋子:皇帝(彼国自称皇帝,中原的档案文献中称之为国王)在高大的象房里与中国来的天朝使臣下了一番辛苦的象棋——在彼国的喃文古籍中,象棋依越语语法,中心词前置,写作「棋象」——说辛苦,不止是因为天气炎热,气味不好闻的缘故。此外,在交趾,还经常有用人来下棋的——我指作为棋子的乃是三十二个活生生的人,「將」于是成了真的将军,「兵」也果真是兵,只是不玩真刀真枪,不收割真正的生命——两两相对之间,隔着真正的河流,纵横的线路都成了隐微的隐喻。
人走的象棋、大象走的象棋与棋子在棋盘上走的象棋,风貌与气象自然各不相同。但呼喝起来,却总是雷同的术语:要想挪动「象」这个子,请用「飞」这个字吧。我一时没来得及考察各地方言,但不管是移象、上象、走象、跳象、动象、行象(你说的是形象么?)、架象(你难道要赶大象上架不成?),似乎都没有飞象那么飞身护主,有慷慨赴难、万夫莫开的气势。但问题是,象能飞么?「马走日,象行田」——这是「象棋」而不是「相棋」的另一重旁证。一如马前有子可裹足,田心塞上他子,可绊住象腿使之动弹不得——但以大象的四条粗腿,离开地球再马上重重地回到泥土表面,那就会生成一个田字的印记。但说到要让它飞?你会说:它连楚河与汉界都过不去呢……
不过,我要说,还真的有屈指可数的几头大象曾经飞过。我曾经满世界地考察飞象的问题,连日本当代漫画家公子正也的《三国志》插图都不放过。我认为,那幅画中诸葛亮神色凝重地端坐在象脖子上,从画面中注视着观众,象脚所在却不在观众的视野中。但从象牙下面和人背后面的红色鸟儿,我可以脑补出,在漫画家的心里与观众的错觉中,大象此刻身在高空。
最有名的飞象,要数是迪斯尼的马戏团小象呆宝(Dumbo),在年的那部动画电影中,有曲唱道:「我算不上历经沧桑,直至目睹大象飞起。」(ButIthinkIwillhaveseeneverything,whenIseeanelephantfly.)且不说这呆宝是天生奇禀,耳朵特大,非娘胎产道所出,系madein天堂,送子鹳亲自派递,而且幼年坎坷,在不曾青春期发育与大规模增重的情况下,误交鸦鼠,早早觉醒了异能——结局温馨却情节曲折。不管是三国版还是大耳版,甚至在网络上找得到的含有老鹰及苍蝇基因的PS版(它们,以及在骨董中可以找到明清时候有一两件六牙翼象纹的青花,我觉得,但凡在大象身上插翅膀的,已然不算是大象,更何况是飞象了),都是现代的视觉艺术,现代的意象与现代的想象。但其实,安南早在古代即有一头飞起来的象,飘飘然从云端抵达京城。当日虽是早晨,料有众目睽睽,万人争睹;故而交口相传,辗转成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大略如下:
一天,珥河(也就是红河)边上的无赖子阿Q走到山峦重叠的地方,发现这里有很多大象。他便挖了个又大又深的陷阱,在坑口铺上竹筚和青草。三天后,青草还没完全枯黄,终于有一头大象落入陷阱,象头冲下,屁股朝天,动弹不得。阿Q用土埋住象身,只露出肛门。然后回家,天天走来看看,自言自語:
——阿Q啊,我会有一头飞象,周游天下。
大象死了。乌鸦、鹞鹰种种闻到腥臭味,便都飞来啄食。它们呼啦啦钻过肛门,进入象肚。先是十来只,后来呼朋引伴,多至成百只,每天都在里面痛痛快快地啄食象肉和内脏。
等到象肉差不多吃光了,阿Q突然塞住大象肛门,挖起土,把大象放平了,骑上去,用棍子在象肚上轻轻一击。里面的鸟群被惊动,都拍打起翅膀,拚命地往上飞了起来。于是,象身带着阿Q飞上天空。俯瞰着下面锦绣一般的山峦河川,阿Q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整整飞了一天一晚,最后,在清晨时分,飞到了京城上空。但见都市恢宏,房屋栉比,人来车往,络绎不绝。阿Q很想下去看看,便在象背上拍了几下,鸟儿们已知厉害,纷纷收翼停飞。象身遂徐徐下降,落在正在朝会的宫廷中央。
皇帝和百官突见有人骑象从天而降,以为天神下凡,敬畏万分,连忙下跪膜拜。皇帝亲自将阿Q送入内殿,盛宴招待,侍立一旁,竟不敢平起平坐。阿Q于是神吹海夸了一番。皇帝颤巍巍问道:
——敢问天神,您能让寡人骑上神象,去看一眼寡人的大好河山,好吗?
——陛下啊,当然可以。但你要做两件事:首先,皇帝你得跟我换衣服,因为神象怕生;
再者,等飞到海上,记得要打开象屁股的塞子,让它喝水。
皇帝连连点头,心想竟用屁股喝水,真乃神象也。他执意不听朝官劝阻,一个人兴冲冲骑上神象飞上天空。到了海中,皇帝想起了阿Q的吩咐,打开象屁股的塞子,鸟群哗啦一声飞了出来,四散而逃。空空的象皮于是掉落大海,皇帝葬身鱼腹。而在京城里,阿Q龙袍加身,登基治国。
将这个只在故事里做了皇帝(该人不费兵卒夺得大宝,可谓之和平演变)的无赖子主人公唤作阿Q,可不是我的发明。在不同的汉文文献中,他被记作阿桂或者阿贵,与鲁迅在《阿Q正传》序中所说如出一辙,我在这里索性效仿文豪的思想,以Q标音,使浙江之古越与安南之雒越遥相呼应,让这个故事与那篇小说在意义与声势上彼此重叠。我曾在德国的《敏斯豪森历险记》中,发现过一个吹牛皮的故事,也将一头活生生的动物变成空心的飞行器;但那里使用的只是气球与飞艇的原理。至于要说到驱使一大群动物来作为飞行动力,舍此之外,我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过。适才我提到,古典时代飞象史,目前为止,以我所见,仅此一例,虽有赶尸控偶之嫌,却想来并无象巫蛊降头那般的诡秘与怪诞感。
汉语中的「想象」以及「幻象」、「意象」种种词语,其本义真的与大象脱不了干系。《韩非子》在〈解老〉一篇中说到,中原地区的人很少能够看到活的象:除非是传说,提及虞朝的天子大舜死了之后,他的弟弟为之耕种田地,舜弟就名叫象;或者是活石,在黄河流域,多年以后也能挖出黄河象的骨殖。象骨及其图形曾经遍传四方,人们就此臆想着传说中的巨象到底长什么样子:也许有的人想象是一堵如高大肉墙般的生物;有的人想,象应该有如巴蛇,彼此呑噬,并能呑噬万物甚至自己;有的人想象会是细似绳索,柔若线头,它身上蕴含着进化的奥妙;还有的人想,象可能是给予蒲扇发现者仿生灵感的源头,柱子发明家学而习之的榜样;甚至有的人看到骨头象,想道:这不是当年被夏朝的天子大禹屠杀灭族的防风氏啊,孰为来哉,孰为来哉,是来向考古学家反驳文献,述说真象的么?……
你或许看出来了,有很多……好的东西混进来了——参见〖麒麟〗——但这却是想象的本象,不是假象与幻象。就象被安南那个阿Q骗进象肚子的那些鸟一样,杂乱参差、种类纷繁不一,方向无序,目的各不同,设若没有一个厚厚的外壳作为表象,即作鸟兽散。
你或许要问,为什么独在安南地区有飞象的故老传说?自然与那里多象有关。最早的字典,东汉许慎所撰《说文解字》说到「象」这个字时,就是这样表述的:「长鼻牙,南越大兽。」也就是说,那种南越的大动物才叫象。南越得自同名的政权,汉初一个叫赵佗的河北人在岭南与中央王朝分庭抗礼,核心区域在交州即今天的河内与广州之间移来移去,传承数代,汉武帝时被伏波将军路博德所灭,其地分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等九郡,大略是今之广东与海南(旧称粤东)、广西(旧称粤西)和越南(粤与越通)北部,而安南历史上,一直有将南越树作正统祖先的企图,曾向作为宗主国的清廷申请把「安南」这个国号改成「南越」,算是复其旧观;但被雍正帝驳回,称南越本中华故土,不止于你邦一处;若让你更名,是不是更会向我讨要两广之地呢?孰料安南的君臣很聪明,不死心,再来了一本上奏,那不叫南越了,改叫「越南」,总可以吧。北京的皇帝不懂比较语法学,嫌其烦,挥挥手,只要不叫南越即可。没想到,如我前文提到,中心词前置的越语中的越南,依然还是南越呵。
至于安南人以象作棋,以及下人棋种种,也许亦可算作刚才那个问题的旁证。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象棋一项,如果剔除日本将棋及高丽将棋这样的变种,若西洋象棋也不算,那除中国外,唯一的强国也就是如今的越南了。甚至他们的西洋象棋也时有大师冒尖于国际大赛——他们多的是象,和在棋盘上执象飞上飞下防御有道的人。
所以,往安南想象,任由思绪飞,那一定是想对地点与方向了。
安南齐天大圣之未遂,
一个名叫强暴的大王
(选自《安南恠谭》)
强暴并非总是动词。可以是一个形容词,然后可以把形容词当作名词用——我说的就是强暴大王。大王一辞,在中国和安南民间,既可以指占山的贼寇,以及远来平定兼带着横征暴敛的民牧藩镇;也可以指吃人或者吓人的老虎,以及护佑生灵但也可能作祟一方的各色神祇。
那个叫强暴的大王乃安南民间一个著名的传奇角色,他曾经是一个人,生过,死过,在安南国山南省天本县贝锦社。至于他的姓氏、家族、父母,几乎都无从稽考,只有他的母亲被稍稍提及。一个平凡的安南妇女,无知无识,有悲有欣,在传统的伦理与生活方式中厕身过了单薄的一生。早年,当她双颊还红润、红润的双颊还充满欢笑的时候,就生下了这个后来被称为强暴大王的独生子。据说,在发现自己怀孕前的一天晚上,与几乎所有传奇人物的母亲一样,这位二八年华、已为人妇的女子做了一个奇异的梦,梦见一个自己从不曾见过的黑大汉不知从何处而来,居高临下地迫近她,让她深感不安却又无以抗拒,但黑大汉并没有做什么特别放肆的举动,只是盯着她看了许久,抑扬顿挫地说了八个字,一句她听不懂的话,然后放声大笑,踪迹皆无。
她惊醒过来之后,还牢牢记得那句话,并且没有因为接下来数日因月信不至、精神萎迷、反胃呕水,发觉自己怀孕而将它置于脑后。她奔回邻村娘家,向自家兄长依声摹拟了那八个字,问他讨主意。她的哥哥算是个读书人,前两年科举不第,心灰意冷,正替富家课儿算账维生,一听妹妹的话,眨巴着眼睛想了半天,说:「那是儒字啊,你遇到神灵了。」所谓儒字,是安南对汉字的称呼。这位未来强暴大王的舅舅翻箱倒箧,找出一本《诗经》,破译出那八个字是:「维岳降神,托生伊族。」说的是有一个顶天立地的神灵,要托生到她家了。果不其然,十个月后,一声儿啼,强暴于焉降生,而他母亲的苦日子也就宣告开始了。
强暴一直不是孝子,他始终忽略父母的要求,即使在他们死后。两个年迈的灵魂从「老有所养」盼到「死有所祭」,理想一个个破灭,在地府里久久不能安息。他们只生了这一个儿子,而他又从来不忌腊和祭祀。一怒之下,竟写了一纸状书,把已经成年、成了孤家寡人的强暴告上了天庭。
事实上可能是误会。强暴生来眇觑一世人,即世界上所有人都不在他眼中,父母也不能例外。但他自幼喜欢耕耘和种树,这个在安南当时显得十分怪异的癖好,后世却被其信徒称之为体现其「屹然有巨人志」。他几乎不拜所有鬼神——也不知道当初他母亲为何会有此托梦,那个神灵黑大汉不知从何处而来——藐视权威与信仰,但却天生对灶君情有独钟,即使捕猎到一尾小虾,也要先在灶君像下供一供再吃。这令卑微的灶君十分感动,据说经常在他面前显露身形。
话说,强暴的父母告上天庭,天帝微哂,天下居然还有如此不孝不敬之人,这还了得!即刻吩咐把雷公找来,命令祂去一个平空霹雳打死强暴。那时候正值冬季,天使好不容易找到那位正在休养生息的雷公,这就给了灶君充分的时间,下凡将天庭的举动一五一十告诉了强暴。强暴听了,气得暴跳如雷,念着已故父母的名头说了好些悖逆的话,估计那两个寃魂在地府因此会面红耳热,连打喷嚏吧。突然他话锋一转,语气平和,婉言向灶君求计。灶君得意地说:
——之所以来告诉你,吾神自有妙计。你该在屋顶上涂满滑不溜秋的东西,让那个尖嘴猴腮、小人得志的家伙没有立锥之地。他纵有火鞭石斧和雷锥电锯,又能奈何呢?
强暴一听,欣喜不已。他熟悉大大小小无数种植物,几经尝试,决定将葫葶捣烂之后,与水和油按秘密比例调和在一起遍洒在房顶上。刚洒完回屋歇着,就见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雷公从天而降,打算蹑在屋脊上,来一个近距离放电,以确保精确打击。没料到一没站稳,竟滑倒到了地上。祂赖以谋生的工具散了一地。强暴见机,突然冲出,挥起棍杖,一顿饱揍。但他没料到雷公还会隐身术,祂抱着头转瞬就不见了,身边的那些锥、锯、鞭、斧也一件件地跟着消失,等强暴回过神来,只抢了一根一丈多长的赤铜绳,遂将其埋在茅房的墙根下。没多久,那绳子就烂光了,只在茅房的土墙底部留下一些蓝荧荧的痕迹,这是后话。
雷公落荒而逃,仓皇而归,遂省略了自己的疎忽,具实向天帝禀报说,那下界的贼汉如此如此了得云云。昊天上帝动了真怒,说:
——三才之中我为尊。你展我威能,震我威声,从来无坚不摧,无刚不折。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竟能与霹雳手相抗衡?
祂顿了一顿,喘了口气,又说:
——莫非这人会五行属火的秘术?那你去把水神叫来,让他择日引洪水,将那个小贼淹作鱼鳖之饵吧。
雷公衔命而去。而这当然又落到善于打听的灶君耳中,祂转身就把消息传报给了强暴。
强暴遂砍下家后的芭蕉树,将树干捆成了木排,取蕉叶插在木排上当作旗帜。到了灶君说的那个日子,大雨滂沱,洪水果然汹涌而至,把村邑中的房子都浸没了。但强暴却在这次无差别的大规模攻击中逍遥自在,他登上了木筏,顺流逐浪,甚至,他事先也没忘记往木筏上搬一套锣鼓响器,这会儿在水面上纵横往来,竟抽空手脚并用,敲击出震天的声音,并呵呵大笑,大言炎炎,向着雨云和洪峰来的方向吹气发出嘘声,宣称:
——我正在与天交战,胜负未果,要不要赌上一把?
这动静,不仅洪水中载沉载浮的幸存者都听见了,连天庭上都一清二楚。
那时候天帝正和群仙一起讨论人间善恶的根本命题,圣谕竟被这不成章法的鼓点打断,龙颜颇为不悦,问:
——哪里来的嘈杂声?
众仙面面相觑。一旁的雷公凝神一听,向上禀告:
——就是那个强暴的贼汉。那天从我的天罗电网中逃走了,如今看来,水神也不是对手,还说出这等干犯天常的反动话,恭望定夺,以儆效尤!
天帝陷入沉思,楞了很久,才说:
——这真是个无法无天的人。如今气焰正嚣张,强行压制,反倒让上天成了强暴,也不是天道所为。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们等等吧,看他不会有好下场。
祂朝雷公吩咐说:
——你有空就去远远地打打雷,虚虚实实搔扰他一下。不过这会儿就去让水神把洪水撤了吧,你看,一场洪水死了那么多无辜的性命,可怜哪。
自此,强暴知道上帝的一言一动,都会经由灶君传到他的耳中,都会上有决策下有对策,于是变本加厉,益发傲慢无理,更加强横暴悍,还越来越喜欢耕作和植树了。他对灶君怀有深深的感激,但在这种情况下,百密不免有一疏。有一天强暴在地里锄作,看见刚下过雨的沟渠里有一只大螃蟹。他的肚子马上就咕咕叫了起来,容不得它反抗,伸手就将这个水神的藩属捉了过来,在田埂上生起一把野火,自炙而食,吃得津津有味,始终没有想起灶君来。
灶君不禁气得肚子咕咕叫了起来。祂本来就有点恼怒强暴在芭蕉筏子上大言炎炎,生怕他大嘴一咧走露风声,心和胆那时候都悬到了嗓子眼。这田蟹的事件让祂下定决心要中伤和报复了。一天,祂在强暴面前显灵,说:
——明日雷公又要来打你。
强暴其实一直挺害怕雷公的,慌忙问计。灶君道:
——吾神自有妙计。你得装作不知道,别像上两次那样,若是被哪个多心的神看出端倪,你是有所准备的,那我们都得玩完。也不是说无所防备,很简单,你可以像往常一样去田里劳作。这不是碰到收割脱粒的时候嘛,若是看见雷雨来了,不要怕,立在地里,把连枷也竖起来,然后两只手伸到连枷的缝隙里;嗯,事先还要往头上套那个你捕鱼抓虾捉螃蟹的鱼篓子,雷公就不会打你了。他的视力有点问题,会把一粒粒稻谷都看作鸡蛋大小,本就不敢打,更何况水神是他的兄弟,鱼篓子里都该是水中的鱼鳖,雷公闻着腥气就认不出你了……
强暴像往常一样,依计而行。没想到这次是灶君编了半真半假的谎言来害他的,等到雷雨漫天而至,他想走,心急慌忙间却怎么挣脱不开那一柄叫「连枷」的脱谷粒用的农具,竟然被雷打死了。半空中的雷公见强暴成了一段焦炭,咕哝着打出最后半个雷,就消失在天际,向天帝奏功去了。雨过天晴。据说,就在那时候,十里八乡的牛一齐挣脱了枷索,竞相奔向强暴的田,齐聚在这里,用脚把四周踩成泥淖,用角把土培成一个大坟堆,将强暴的遗体深深地埋藏在下面。
而这些牛的主人蜂拥找来,其中有通灵者得知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广而告之。人们深深敬畏死者不敬天地、不畏雷火与洪水的往事,遂燃起香火,宰牛献果,就此将他供奉为大王。此后几百年间,他们既来此拜祀强暴大王,又回家虔诚地供灶敬灶送灶迎灶,还会每年每岁在固定的日子祷天祭地,以及雷公水神等等一干仙祇,谁都没有拉下。据说,强暴大王也常常会在信徒们面前显灵。只是,有关祂和天帝、灶君、雷公与水神间的恩怨纠葛有无续篇,竟没有一个人、一本书再提过半句。
◎珐案
材料来源:《公余捷记》、《神怪显灵录》、《越隽佳谈》前编、《南天珍异集》卷二以及《越甸幽灵》的一个抄本。
有关强暴大王的母亲几岁怀孕生子,诸本有异说,多半称只有十五岁,这在古时的热带当不足为奇,但《南天珍异集》称是五十岁——也许是抄错了,但也不宜轻易否定。安南很多传说都涉及晚来得贵子的情节,譬如状元甲海的母亲,可参看《~》。
这则怪谭差点演绎成大闹天宫,直可惜安南的主人公最终经不住雷劈——关键是他没有一个好师父,更没有一个好出身。
怪谭中那段针对雷公的陷阱以及接踵而至的洪水,在南方的故事里多有所闻。尤其是中国西南诸民族尤其是僮侗与苗瑶语族的神话中,流传着以写作「伏羲」或者「盘古」与「女娲」的兄妹为主人公的洪水神话,说的是大洪水之后,他俩成了孑遗,即唯一幸存的一对男女,无奈中兄妹相婚,再造人类的情节。其中的那场大洪水,就是这对兄妹的父亲与雷公打仗,把雷公如此这般地捉住的后续情节。譬如有一个从广西金秀大瑶山记录下来的版本:
那知雷王不肯放松一时,每天都跑到大圣屋顶上挑战,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几乎把大圣的耳朵震聋,大圣一刻也不得安稳,骂道:「雷王呀,你别猖獗,有朝一日抓到你,我叫你碎尸万段!」他走到河里,捞取很多滑溜溜的青苔,铺在自己住房的屋顶上。不久,雷王又来挑战,从天上飞了下来,一脚踏在屋顶,脚顶未站稳,骨碌碌一个踉跄,啪哒一声跌下地来,大圣用水缸把他盖住,关在禾仓里……打算把他杀死,用肉腌鲊。可是家里没有这么多盐,也没有这么多坛子,于是决定到圩场上去买盐和坛子,回头再杀雷王。临行的时候,再三叮嘱他的一对儿女——伏羲兄妹:「好好看守雷王,不要给他水喝。」(选自《瑶族民间故事选》,上海,年)
其中雷王的大敌竟然就是大圣——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向天宫索要的名头——可惜瑶族的大圣死在稍后的那场洪水中了。而屋顶上滑不溜手,使雷公或者雷王站不住脚的,此处是青苔,怪谭中则谓是葫葶。「葶」字在这里读若顶(dǐnɡ),《广韵》标都挺切,上声迥部端母字,说其为毒草专用的称谓,并举了《山海经》的例证:「熊耳山有草,状如苏而赤华,名葶苎,可以毒鱼。」那种叫葫葶的植物在安南有一俗称,叫梦,从其用汉字「梦」,以及从竹从思思亦声的喃字「」,猜它大概有致幻效果。
上文中的瑶族雷王终被无知年幼的伏羲兄妹私放之,回天之后想要报复,遂发动了洪水毁灭世界。但他顾念兄妹恩情,送了他俩一个大葫芦藏身避世,人类得以重新繁衍,死灰复燃。近世学者对此多有研究,或称葫芦乃子宫象征,或将葫芦与《圣经》中挪亚方舟相比附。
普世皆曾有雷乃天神之威的观念,比起安南,从犹太的耶和华、希腊的宙斯、印度的因陀罗到东方,更多民族的至高天神都自身蕴有司雷电的神格。「神」字在汉字中本作「申」,与「电」同源,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俱以闪电之曲折蜿蜒来象形。
从这则怪谭所见,安南则有将闪电理解成那段被强暴抢夺下来埋掉的赤铜绳发光的缘故。我则从它联想到现代社会才有的电线——它们都是通电的铜线,只是如今不裹以絶缘层的裸线很少见了,我小时候还常见有伙伴不知从何处弄来一段长长短短的剥了皮的铜丝把玩。这两年的孩子大概不会再有类似玩具,而我在网上和野外都见过这样的标语牌,竖在草丛中,上书:「光缆没有铜,偷了也没用。」
在我童年,雷神被称之为雷公公。记得在夏日的晚饭后,我和妹妹坐着矮凳,在屋前的空地上吹着几公里外杭州湾的海面上刮来的风。祖母摇着蒲扇赶蚊子,给我们说一些简朴的童谣与悠远的故事。有两次隐隐从远方的天际传来雷声打断她的话头,那时候祖母眼睛虽已老花,耳朵却依然聪敏,她会说:「听见没?雷公公发脾气了。」「雷公公为什么发脾气呀?」那时候妹妹还小得什么都不懂,吃饭总是绕着桌子乱跑,要大人端着碗追在身后,直到纳凉时才安静地坐下来。祖母告诉妹妹:「因为有小孩子不好好吃饭哎。小孩子尤其不能浪费粮食。」然后她转过身来跟我说:「要把碗里的米粒吃干净,不然雷公公会打的。雷公公在天上什么都看得见,但我们做的好事祂十件都记不得一件,而一粒米在祂的眼里却像一个鸡蛋那么大。要是我们浪费一粒,祂会很生气地记在心里。浪费多了,祂就会觉得这个小孩是个坏人了……」我就此对这个有特殊透视原则的小气雷公公印象深刻,即使到了不信故事的年纪,还依然习惯把碗里的饭吃光光。怪谭中说到雷公视力变态,实是从吴越之地借调到雒越的一个细节,原先的各个钞本上并不曾提到过雷公把素的米粒看成了荤的鸡蛋。
这就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雷公公版本。但惩戒固是雷神的权柄,监察更多时候其实是灶神的职能。在汉文的传统中,灶神早在汉代大概就已经与司命神合二为一,常被称作「东厨司命」,而司命的方式也就是平日一言一行都洞若观火,有没有玩弄婢女,有没有腹腓圣贤,有没有为富不仁,有没有丢人现眼……看得见的,以及看不见的罪恶都具体而微记录在案,而到了每年的腊月二十三,上天禀报天庭去也。是以祭灶时候各地皆供以糖饼,旨在粘其嘴;灶君的各种木刻画像上也大都写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之类明明白白的祈愿。
因此在这里安南的怪谭中,灶神并不是偷偷站在天神的对面,其实是与雷公与水神相抗——那两位抢了祂的饭碗。灶神与雷水二神之间的龃龉由来已久,可与大量的巫术氛围中的古老习俗相印证:祭灶信仰源自火塘崇拜,其根柢在于人类对自己能够利用而未必完全控制的火的信仰。是以《礼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典籍记载,早期的灶神曾经就是炎帝或者火神祝融。是以灶神具有火神的神格,而火神与水神以及引发水——尤其是暴雨所致山洪的雷公素是对头。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爵士的名著《金枝》中用整个欧洲、阿拉伯、印度到印度尼西亚的多个例子说明:先民们普遍认为,点火、持火、烧起篝火可以在雨季中驱雨和防御雷电;而在旱季中则又可以藉此来祷雨。譬如:
在印尼托拉杰人那里,司雨巫师的专门职业就是赶走雨水,……在村外一块稻田里给自己建造一间小屋,在那儿他燃起一小堆火,而这堆火是绝不能让它熄灭的。他在火中燃烧各种据认为具有驱雨特征的树木,并向着雨云迫近的方向吹气。(引自《金枝》第五章:巫术控制天气,中译本,北京,年)
按照人类学家的提示,怪谭中强暴遭致雷打水淹,其实可以说是灶君引来的呢。
也许有读者会质疑,至少我就猜忌过:何以灶君曾独独青睐强暴呢?这与强暴信仰灶神有关。灶神信仰,有学者曾感叹过,其沿革之曲折变化,乃是任何一位原始神演变成民间迷信中的俗神都未曾有过的。这说的是灶神信仰在东方极为复杂。安南与中国一样,灶神多有三尊并祀、三位一体的现象,但在安南,祂们被呼为「本家东厨司命灶府神君」、「本家土地龙脉尊神」、「本家五方五土福德正神」。皆有「本家」二字,言下之意是指各家有各家的灶神。这是道教的观念,安南也有道教,虽与北方略有不同,以玉帝女儿柳杏公主为主神,称母道教,但不管是名义、还是神谱、仪轨,皆可以看出与道教的一脉相承。据现代学者李叔还所编《道教大辞典》的说法,信仰道教的地区,「各姓所祀灶神可以是本姓祖先之有德者任之,以察其子孙之善恶,故俗又有称灶神为本家司命。」所以每一家的灶神面目可能是各不相同的,一如每一个家庭的美味和命运往往有差异——而美味和命运正是灶神所司。所以那个喜欢强暴的灶君,也可能只是强暴家的灶神吧。
而且这位灶君极可能是位女神:宜称灶妑或妑灶(BàTáo),也就是灶婆的意思。汉地的三位一体灶神组合基本上是一夫二妻,齐人之福的造型,但在安南通常却是一妻二夫,一位灶婆配上两位灶翁(?ngTáo),统称灶君(TáoQuan),并对应上文的三个「本家司命」,其中尤以女神灶婆为主——跟前文谈及安南的母道教特色又颇可呼应。且有民间故事讲述其由来:
这位灶婆原为是位贤惠而且旺夫的女子,名叫侍儿,在故事开始的时候,她与丈夫重高过着幸福而富足的生活。孰料重高后来竟染上赌瘾,在牌桌上连连受挫,迁怒并归咎侍儿,将她扫地出门,弃若敝履。侍儿在路上得到一名叫范郎的贫穷男子照顾,日久生情,两人成为夫妻。范郎在侍儿的帮助下,没过两年,竟成一方富户。而这时,重高已经输得精光,一贫如洗,竟沦落为丐。重高四乡乞讨,遇见了行善布施的侍儿,认出竟是自己的原配,羞愧不已。侍儿也认出了前夫,将他唤回家中细细询问近况。这时,恰逢范郎回家,为避误会,侍儿将重高藏身于稻草堆中,孰料不知情的范郎误燃之,竟烧死了重高。侍儿深感痛悔,赴火自杀,以示一命还一命;范郎亦惜妻死,随之蹈火。天帝感其恩重情深,封他们三人为灶神云云。
安南的灶神还有一点与北方不同,一位灶婆和两位灶公也被称为土祇、土公和土地,也就是说,祂们并不像北方那样强调灶神与司命神的并流,而是把灶神与土地之神两种神格合二为一了。这大概与安南地处热带,食物多土中产出,生食熟食皆可,是以有火没火差不多——灶神的「灶」字把火字去掉就是「土」字了。而灶神之主是女神,谓土祇,其实也就是地祇,这与天神之间其实也就是天公与地母的翻版。在世界上各民族的神话中,天与地之间大部分都有男神与女神的性别配合。祂们各有班底,一个要打杀,一个要维护,帝党与后党之间的倾轧,在希腊神话中也多的是。有时候,在安南这天与地的性别则未必很明显,或者说这一对至大至尊的男神女神的体位并非固定不变的:在越语中有一个古旧的词叫?ngT?o,与「灶翁」仅是声调上的差别,对应成汉字可以写作「翁造」,是造物之神的神格,如今可以译作造物主。
在抄录这则怪谭的数种安南旧籍中,独《越甸幽灵》中即称「土神」而非灶神。而其他情节,这一本与正文所见亦有区别:土神教强暴在屋顶铺的是几层「流涎菜」,并告诉他,雷神唯一所惧怕的是雄鸡——那样,雷神倒像是蜈蚣、蝎子等等毒虫之属了——祂建议强暴赶紧去买一只养着,到时候趁雷神滑倒,鸡啄杖击,即可制服。果然就这样抓住了雷神。那是深秋的事情,但《越甸幽灵》没有交代接下来怎么处置雷公,祂是不是趁机逃走等等,而径直跳到春耕时节,强暴疏忽,居然一个人把那雄鸡杀了炖成一锅,有滋有味地吃个精光,压根没想起土神来。土神于是怒极,怂恿他造反,强暴信了,结果还没有发动起声势,就被闻讯而来的大军剿杀在了水田里云云。这个不一样的强暴,姑且立此存照。
——“比希摩斯的话语”是由诗人王炜编辑的一个关于诗艺和文学、思想史、亚细亚现实观察的订阅号,不定期更新,希望持续呈现一种文学传统和智识视野,也呈现当代中文写作者的工作。
在《约伯记》中,代表陆地力量的巨兽比希摩斯,与代表海洋力量的巨兽利维坦对应。霍布斯年在针对另一个写作者Bramhall撰写的小册子《关于自由、必然和偶然》的评论中写到,要反驳利维坦,“比希摩斯对抗利维坦”将是恰如其分的标题。比希摩斯也成为霍布斯另一本著作的书名,在这个标题下,霍布斯对—年间的革命进行历史描述。比希摩斯被霍布斯用来象征无政府状态,同时,利维坦意谓国家,比希摩斯意谓革命。不过,在其他的许多书籍与阐释中,比希摩斯与利维坦的形象各自具有众多变体,两者的关系也充满变数。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wugonga.com/ammj/63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