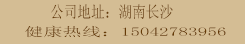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蜈蚣 > 蜈蚣的形状 > 野客怪谈下雨夜荒庙发生怪事,书生酒
当前位置: 蜈蚣 > 蜈蚣的形状 > 野客怪谈下雨夜荒庙发生怪事,书生酒

![]() 当前位置: 蜈蚣 > 蜈蚣的形状 > 野客怪谈下雨夜荒庙发生怪事,书生酒
当前位置: 蜈蚣 > 蜈蚣的形状 > 野客怪谈下雨夜荒庙发生怪事,书生酒
这是「怪谈文学奖」推出的第95篇故事
这些故事试图讲述生命中那些幽微的部分
希望这些故事能为您带来阅读的愉悦
并让您感受到世界的广阔
今天的故事是《野客怪谈》的下篇,仍由「余观鱼」讲述。
《野客怪谈》上篇传送门:
野客怪谈:雨夜荒庙发生怪事,书生、酒家女、和尚、樵夫、丝绸商人用故事拼凑线索怪谈文学奖
小老儿我姓刘,今年正好六十,家就住本地,乡亲都叫我刘老汉。我平日以打柴为生。我和老妻两个日子虽贫苦些,倒也知足常乐,只是可怜我们半辈子没有孩子,到了四十多岁才得了一个男娃,真真是视若珍宝,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我特地请乡里有学问的先生给他取名,叫作刘蕴玉。
我思量着乡下人家,若不读书,一辈子目不识丁,也只能打打柴、做做仆役了,于是便拿出半世积蓄,供他读了几年书,也考了一次,没有中。
小儿只平日在家读书,也难免清静。乡下人家,谁家小子不是十二三岁就出门讨生活,偏我家的十七岁还像菩萨一般供在家里,左右邻居便多有些酸言酸语。我那小儿最是要强,一日,他对我说:“人都说自古读书皆是为了科举,孩儿不这么看,读书是为了明理修身,那孔圣人时哪有科举。孩儿虽科场不利,可天理人伦也是晓得的,平素为人也不曾做有损德行的事。如今我赋闲在家,街坊左右多有口舌,不如索性放孩儿出去历练历练,也免得爹爹年近花甲,还如此辛劳。”
几月后,族里有人要出海做生意,那船老大见我儿识文断字,为人又老实忠厚,便让他在船上管账。
那日我送玉儿远行,山里路难走,我们半夜便启程,一前一后两盏灯笼。俺老汉说不出文绉绉的话,只是家常话叮嘱了三五句。
其实,又何必我老汉叮嘱,那孩子心里透亮,都明白着哩。
行到半山腰,四下黑漆漆的草木里,忽然传来老翁的咳嗽声,我儿道:“爹,夜里风露大,您就送到这里吧,免得受冻着凉。”
我知道我儿是把那孝子催听作我在咳嗽了,我笑道:“儿啊,你看我年纪虽大,可身子骨还硬朗哩。你刚刚听到的不是我咳嗽,这是山里的孝子催啊。”
你们问啥是孝子催?各位不要急,容我老汉慢慢说。
山里人走夜路,经常会听见周围有老人的咳嗽声,那其实是山里的刺猬叫声,年轻后生听了,难免会想起家中年迈的父母,赶路时少不得要加快速度,所以山里人都把刺猬叫声叫作孝子催。
我儿听了这孝子催的来历,心里触动,又说了好些宽慰我的话。
一路上就这样,走到东方发白,走出了大山,各自挥泪作别。
回家后,我那老婆子就整日絮絮叨叨,说我不应该放儿子远行,我知道他是思念儿子。
好在我那儿子短则半月,长则一月必有书信寄来,连那代人写信的先生都夸我家玉儿是个孝子。
可惜,好景不长,半年后,我听人说,那船老大运送货物,去时还好好的,哪知回来时起了大风浪,将那船打沉,一船人怕是都葬身鱼腹了。
我听了这消息,吓得眼前发黑,也不敢和老婆子说,只是背着人暗暗哭几声。
可是年关将近了,我儿还没有回来,眼看着就瞒不住了,哪料,我儿子就回来了,我真是喜出望外。
老婆子见儿子瘦了,忙去杀鸡要给儿子好好补补。安顿好行李,我便问他这大半年来的经历。
原来,那日船被风浪击沉,他侥幸抓住了一片木板,在海上漂了几日,后来为山东一渔民所救,休整几日。由于身无分文,便到兖州一富户家做杂役。后来得到主人赏识,便成了管家。
说话间,老妻已经炒好小菜,端上饭食,一家人其乐融融。这且不提。
欢欢喜喜过完元宵,我儿便又去了山东。
这一去便又是大半年,我老夫妻两个虽担心他孤身在外,难免辛苦,但毕竟知道他在何处,所以多少也还安心。
哪知,一日,几个差人找到我家,自称从山东赶来,说我儿在兖州犯了命案,现今被关在大牢里。
我只好宽慰老婆子几句,和他们同去兖州。一路上我只疑心他们弄错了,想我儿平日为人,怎么会犯命案?
到了兖州大牢里,我看见我儿一身囚衣,带着枷锁,坐在牢里。见了我,只是冲着我磕了几个头,流着泪道:“爹,孩儿不孝,要先走一步,不能给您和娘送终了。”我听了,真是肝肠寸断,当下就眼前一黑。
待醒转来,已是在客栈,身边两个衙役告诉我,我儿子在那富商李家当管家,可七日前,我儿子用毒鸡汤毒死了李家老爷,逼李家夫人改嫁于他,妄图侵吞李家家产。
那李家夫人誓死不从,后来被人撞破,便到官府自首了。官府老爷见情节恶劣,便就判了秋后问斩。
得知此事,我老汉几乎哭瞎双眼,想我与我老伴大半辈子才得了这一个孩子,如今却要白发人送黑发人,我怎么不痛。
时间无情,一天天就这样过去了。
临刑前夜,我带了酒食去送我儿,我说:“孩儿啊,他们都说你杀了那李家老爷,可我始终不信哪,你是不是有什么冤屈啊?说出来爹去衙门给你喊冤。”
他却对我说:“爹,这是孩儿错了。有些事情,孩儿涉足太深,已经无法回头了,那人也不放心我活在这世上。不过爹你放心,我走之后,每月自然有人会给你送银子,只是要劝娘切莫太过伤悲。”
我道:“那人是谁?可是他害得你这样?”
他却只管吃菜,什么也不说了。
唉,秋风过了,那长了一个春夏的苗木就枯了,大刀过去,那养了十几年的小子就没了。
回家之前,我去了李府,我知道一定是那李府的人害了我儿子。
那李府深宅大院,青砖高墙,朱红大门,气势恢宏。我不敢靠近那大门,便到侧门去痛哭了一场。
正待要走,那侧门却打开了,出来了几个年轻女子。
为首的那个一身孝服,素净脸庞,但通身的气派,一看便是大户人家的夫人。后面跟着几个小丫头,都在抹眼泪。
我偷偷凑近了些。听见一个丫头哭着说:“夫人,你何苦这样,把那家产白白让与那狼心狗肺的吴徵卿?”
那夫人淡淡地说道:“钱财也不过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既然他要,给他便是,李郎已经去了,这里我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
“夫人,你打算去哪里呢?”另一个年纪大些的丫鬟道,“把我也带走吧,我是卖给李府的,而今老爷去了,李府易主,我点翠就是死,也不会认贼为主。”说完便拉着夫人的裙脚,跪下了。
那夫人叹了口气,没有说什么,扶起那丫鬟,主仆两个相扶着走远了。那些丫鬟目送着,直到看不见那二人,便回身将门关了。
第二天,我归去时,路过那里,李府的牌匾已经被人摘了下来,听过往的人说,这宅子如今已经改作吴府了。
(众人听到这里,见老翁似乎是不想再讲下去,都有些急了,那老翁叹了口气,接着讲了下去)
回了家不到一个月,果然有人给我送银子了,那人自称李文,曾与我儿一同给李家办事。他告诉了我真相。
原来,我儿在李家做事勤勤恳恳,认认真真,但这府里有个乐师,时不时巧立名目到账上支钱,偏偏我儿心眼实,每个账目都对主人如实相告。一来二去,他就与我儿结了怨。
那姓吴的一心想挑我儿错处,于是便暗里找人盯着我儿,毕竟人无完人,终究被他发现了。一次我儿算账,错了五十两银子,告诉了东家,偏那日东家与夫人闹别扭,喝了酒,便叫那姓吴的处理。那姓吴的便一口咬定是我儿子偷了那五十两银子,一定要我儿交出来,我儿哪里有这钱,无奈只好借了当地恶霸的钱。
后来日子到了,那恶霸便来要钱,说还不上就要到他老家来向他娘老子要。这时,那姓吴的就跳出来做好人,替我儿还了一个月的息。
如此,我儿就算是有把柄落在他手里了。那姓吴的觊觎李家财产和那夫人,暗地里胁迫着我儿做了不少见不得人的勾当。最后,又让我儿当了替罪羊……我可怜的孩子啊。
众人见刘老汉哭得撕心裂肺,一时间都围上来劝刘老汉,唯独那和尚却在一边也暗暗地抹眼泪,那商人奇怪地问道:“小和尚,人家刘老汉哭他儿子,你又为何而哭?”
那和尚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小僧想到家中也有年迈的父母,可如今,因小僧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带累双亲为我蒙羞。想到这里我就羞愧落泪。”
那商人道:“小和尚,你年纪轻轻,犯了什么罪孽?”
那和尚叹了一口气道:“一言难尽,这一切都要从一颗小小的豆子说起……”
小僧法号无尘,今年二十,家在敦煌,因幼时多病,有高人称我命里有劫,须到佛门净地,才可化解。于是六岁时,父母便忍痛让我在敦煌三界寺出了家。
小僧在三界寺每日诵经,打坐,扫地,担水,日子一天一天,平淡如水。三界寺的方丈为人可亲,只是有一个癖好,那便是喜欢吃豆腐,每日宁可不吃饭,也不能没有豆腐。冬天也好办,多买些存着便是。可是夏日,豆腐容易馊,所以方丈便遣小僧每日去附近镇上的豆腐店买豆腐。
镇上只有一家豆腐店,店里老板是个中原人,祖上迁至此地,便开了这豆腐店,娶了一位西域女子,两人生了一个女儿。小姑娘年纪与我相仿,长得有七分像她母亲,白皮肤,高鼻梁,深邃的蓝宝石般的眼睛,能歌善舞,很是活泼。我买豆腐也时常遇见她。
一日,我如往常到店里去买豆腐,店主夫妇有事不在,只留了他们的小女儿看店。我买了豆腐,正要出门,谁知门口滚了一颗黄豆,我一脚踏上去,摔了个嘴啃泥,手中的豆腐也摔碎了。
店里几个闲汉见了都哈哈大笑,我涨红了脸,爬了起来,不想一脚又踩在半块豆腐上,又跌了一跤,那些闲汉见了,几乎要笑破了肚皮。
我窘迫得几乎站不起来,这时那小姑娘走过来,将我扶起来,我低头道谢,面上火烧般。那些闲汉依旧在打趣,我正打算走,她一把拉住我说:“小沙弥,你莫走,我叫他们给你道歉。”
我站在那儿,如同木偶一般,低下头心里默念佛号,但她牵着我的那只手,好似一块火炭,我的脸烧得更红了。
她拉着我走到那些闲汉面前,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说了些什么,那些闲汉听了,顿时严肃起来,规规矩矩地用生硬的汉语向我道了歉,便离开了店。
看着他们离开,小姑娘冲他们不屑地做了个鬼脸,转头便来看我,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向她道了谢,她转身又取了两块豆腐给我,说道:“小沙弥,你空手回去怎么交差,这个送给你。”
我连忙摆手:“女施主,万万不可,师父说不可随便取人物品。”
那小姑娘眨了眨眼,调皮地一笑:“你们佛门弟子不是有化缘一说,这个就当我给我自己结的善缘好了。”
我只好收了,回到寺里,方丈问起,我便原原本本地说了。不想方丈却皱起眉头,把我叫到房中,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无尘啊,你虽身在佛门,但尘缘未断,你命里姻缘未了。”说着卷起我左边衣袖,露出手臂上那块艳红如桃花的胎记道,“你命中有此一劫,而今倘若留在此地,怕是躲不过此一劫。你收拾好东西,去中原甘露寺投奔明空大师吧。正好也可替我捎些物件与他。”说着,方丈便连夜让大师兄无因带着我离开了三界寺。
我与师兄一路风餐露宿,一路化缘,走了半年,到了甘露寺,见了明空大师,他打开师父让我们带来的包裹,却是几部佛经,我知道那是三界寺所藏最珍贵的几部经书。明空大师叹息着告诉我们:“一个多月前,敦煌周边发生了战乱,中原朝廷鞭长莫及,而今已经切断了与敦煌的联系,只怕三界寺在战火中已化为劫灰了。”
我呆住了,心狠狠地疼了一下,那一瞬间,我所想的,竟然是那个有着蓝宝石一般眼睛的小女孩,明明不比我大,却还是一口一个“小沙弥”,自己那么柔弱,却还要替人打抱不平。
战火无情,不知她是否安然无恙。
明空大师感叹说,方丈是早有预感,敦煌会起战乱,所以将这几部最珍贵的经书送到甘露寺保存。接着又感慨了几句,便让人收拾了几间禅房让我们住下。
住了几日,恰到了秋雨绵绵的时节,那雨整日滴滴答答,夹杂在那木鱼声中,竟带了几分思念的意味。
我思念敦煌的一切,阳光、沙丘、驼铃、三界寺、父母、方丈,还有那家豆腐店。那是我回不去的家乡。
过了不到一年,无因师兄便还俗了。那日,他脱了袈裟,跨上枣红马,向敦煌打马而去,他想去平定那里的战乱。临行前,他在酒馆喝光了一坛酒,他的决心就如同那只摔碎的酒碗,他说:“敦煌一日不宁,我一日不回。哪怕黄沙淹没了我的白骨,我也不会回头。”
送走了师兄,便只留下我一个人默默地诵经,打坐,敲木鱼。又过了几年,明空大师圆寂了。接管寺里事务的是明月大师。
明月大师很善于理财,不到半年便给寺里新置办了不少田地产业,还重新给殿里菩萨镀了金身,庙里香客越来越多。
明月大师为了多些进项,还将庙里空置的几间房子租给了一个卖药的江湖术士。那江湖术士也去过边关,因此我时常过去与他清谈片刻。
一日他喝醉了,向我道:“无尘小师父,依小道看,而今这甘露寺真正有心供佛的,也只有你一个了,那些秃驴供的哪是菩萨,分明是财神爷。”
他说得虽刻薄,可也是实话,如今这庙里香火越来越盛,和尚也越来越多,知客僧就有七八个,可诵经打坐的却越来越少了。
他忽然似乎想到什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道:“坏了,今天我还得去王公子府上把那药送过去……”走了几步,却是摇摇晃晃只在原地打圈,我便道:“不知小僧可否代劳?”
他犹豫了:“这药方子还有不少讲究,若不当面说清,只怕影响药效。”我道:“不妨,你就说与小僧听,小僧一定替你转到。”
于是他又大着舌头说了几句,无非是些用药期间的忌讳。我记住了,拿了药便向王府走去。
到了王府,我将那药交与王家公子,说了几句需要注意之事,便告辞了。出府需要穿过花园,我在那园子里绕了一会儿,迷失了方向,正打算找个人问,面前忽然出现了一片荷塘,塘上有一座石桥,有个女子孤零零地站在那石桥上,看着远方。
我行了一礼道:“请问,女施主……”
她回头,我呆住了。
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何必曾相识。
虽然已经不复记忆中的那张稚嫩脸庞,但那双蓝宝石一般的眼睛依旧那样美丽,只是那双眼睛似乎笼罩了一层淡淡的哀伤。
她看到我,迟疑了一下,脱口问道:“你是那三界寺的小沙弥?”我点了点头:“是。”
他乡遇故人,她的欣喜都写在脸上。虽然久做中原客,但她没有学会中原女儿家的羞涩矜持。她还是那样直率大方,如同一块琉璃,一眼就可见底的澄澈通明。
她吃了很多苦,战火中,一家人在逃亡途中分散,她被人辗转运到中原,被卖到胡姬酒肆当舞女,在那里她与王公子相识,相知,相恋,最后,王公子力排众议,娶了她做正妻。婚后甜甜蜜蜜,几个月后,他便不似当初那么温柔了。
说到这里,忽然,她幽幽地叹了口气:“小沙弥,你说这中原的男人怎么说话不算话?明明当初说好只娶我一个人……”她的声音一点点低下去,那双蓝色的眼睛弥漫了水气。
我沉默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却自顾自说了下去:“他还说等到敦煌战火消了,带我回去呢。可是,现在他却把我一个人丢在府里,自己去那花街柳巷……还把那些人带回来,我用鞭子把她们赶出去,去找王一理论,他却说我是悍妇,就连那些下人都说我善妒,说我心胸狭窄……我做错了吗?可是,阿爸不是只娶了阿妈一个吗?……”
看着她泪落如雨,我心里隐隐作痛,笨拙地为她擦干眼泪,将她轻轻揽入怀。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我大劫已至。她,便是我此生躲不过的劫。
就是那般,暗地里,情种种下,朝朝暮暮,翻云覆雨,那见不得人的相思浇灌出的情根,不知不觉已经是牢牢扎在我心底。
佛说:色即是空。可是纵然是空,我也愿意沉溺其中,红尘三千,本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红粉骷髅,富贵如过眼云烟,我也可以看破,我所迷恋的,不过是有她的红尘。
听说,西方极乐世界有迦陵频伽,歌声宛如天籁,可是即使一万只妙音鸟,也抵不过,枕间耳畔她温柔的低语呢喃。人间有她,便是极乐。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她,我又何必去。
她说:“小沙弥,我喜欢你。我已经放下王一了,随他三妻四妾吧。中原虽然好,可是我想家了,我们回家好不好?”我嗅着她的发香,不假思索地说:“好。”
我知道我已经堕入魔道,也许我死后会落入地狱,受尽酷刑,又或许我会永堕轮回,不得超脱,但是我依旧甘之如饴。
我们约好,一起回家。
可是终究还是被王一得知了消息,他让明月和尚将我锁在庙里。过了几日,明月告诉我,那夜王一追捕她,在林中遇着强盗,所有人都死于非命了,而她则下落不明,有人看见她被一个独臂强盗掳走了。
后来,我到那林子里搜寻了好几天,只发现了一串散落的红豆手链,那是我七夕赠与她的,断了线的红豆,散落在草丛里,好像是谁人的血泪……
众人都叹惋了一会儿。最后只剩了那女子,那女子抿嘴笑道:“各位的故事都精彩纷呈,可惜小女子的故事太过平淡,说出来只怕贻笑大方。”
那书生摆了摆手道:“姑娘此言差矣,殊不知淡极始知花更艳,平平淡淡才是真哪。”
那女子笑了,便不再推辞,说起了她的故事。
小女子名叫艾草,是蜀中人氏。小女子所属部落,便就是金大哥提到的那以蜈蚣为图腾的部落了。
不过金大哥所说的秘术却并非我们部落的,我们红龙族与黑龙族毗邻而居,却世代为敌。两族同样是以蜈蚣为图腾,但那黑龙族利用蜈蚣炼毒,而我们部落则是用蜈蚣炼药,两族都世代居于蜈蚣谷。
外人不明就里,看了黑龙族的人行事阴狠毒辣,便以为我们都是这样。我们也曾受了不少气,于是有人便劝族里的长老搬到别的地方去。
可长老坚决不肯,他说这蜈蚣谷是我们的发源地,红龙族人生于斯,葬于斯。
于是便没有人再提这事了。可是族里的人渐渐也有了怨言,埋怨那黑龙族为非作歹,连累我们,于是两族起了几场大冲突,死伤不少,双方都元气大伤,便也就和睦相处了一段时间。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不知怎么的,黑龙族的人得罪了官府,官府便大肆搜捕黑龙族,那些黑龙族狡诈异常,鲜有捕获,倒是我们红龙族被抓了不少人,官府也不问清楚,只管赶尽杀绝。
到后来,我们红龙族人心惶惶,有些年轻人便离开了蜈蚣谷,去了远方,留下来的人也都东躲西藏。
我的未婚夫是长老的小儿子,叫柏子,按红龙族的规矩,我们的婚礼必须在蜈蚣谷举行。所以我们都不能离开蜈蚣谷。
为了澄清误会,柏子要求与知县谈判,县官同意了,但只能他一个人去。
他出发那日,是那么威风,身上披着我为他织的蜈蚣锦,就去了。
可是,回来的时候,只有一条染血的蜈蚣锦。官府设下计谋,为的是擒贼先擒王。
长老一病不起,族里的人再也留不住了,都各奔东西。
我留在村里照顾重病的长老,他们都说我疯了,就连我的家人也离开了,整个村子几天内就空了。
过了一段时间,长老也支持不住了,向我交代完后事就撒手去了。
又过了几年,黑龙族见风声过了,便回到蜈蚣谷,他们见红龙村只剩下我一个人,都得意扬扬来挑衅,我只是闭门不出。
我一人守着整个村子,一如往常,看到黑龙族祸害外乡人,我能帮便会帮一把。
黑龙族人得意了没几天,便开始愁眉苦脸起来。原来他们的长老炼制毒药时,不留心将毒扩散了出去,大半个村子的人都沾染了毒。他们只会制毒用毒,以毒攻毒,却不会制解药。
我什么都没有说,走到黑龙村,采集了那毒,制出解药,分发给他们。
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年轻人便对我客气了许多。
又过了一段时间,黑龙族因为族长传位之事起了内讧,于是便有一部分年轻人离开黑龙村,住到了红龙村,每日和我学着制药。
又过了几年,红龙村的规模壮大了,与黑龙村又旗鼓相当起来。他们都推选我为红龙族族长,我也没有推辞。
长老临终前告诉我,红龙黑龙很久以前都是一族,后来分开了,可依旧谁也离不开谁,只要红龙村还有一个人,那么红龙族就不会亡。同样,如果红龙族没有了,黑龙族也不能独存……
后来村子里来了几个汉族女子,他们是苏州的绣娘,说是来学蜀地的织锦手艺。于是我便取出那块蜈蚣锦,教她们针法,但她们都面面相觑,不敢靠近。终于,一个胆子大的绣娘道:“艾草姑娘,我们想学花鸟织法。”
我愣了,道:“什么花鸟?”那绣娘道:“鸳鸯。”
“什么是鸳鸯?”我不解。
“就是象征夫妻恩爱的一种水鸟……”那绣娘红了脸,羞答答地说。
“鸳鸯吗?”我放下针,沉吟了片刻。忽然,我眼前闪过柏子身披蜈蚣锦,昂首阔步远去的背影……
众人听了都愕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忽然之间,不知谁说了一句:“你们看,雨停了。”
众人抬头,果然,雨过天晴了。于是各自收拾东西,走出破庙,一同朝桥的方向走去。
忽然,晴空里一声霹雳,众人都吓了一跳,再回过神来一看,哪里有什么桥,面前分明是深不见底的深渊。
再回头看那破庙,原来却是昏昏惨惨的森森阎罗宝殿。
众人皆如梦初醒,回想往事皆汗如雨下,拜倒在阎罗殿前。
这时两个青面獠牙的小鬼抬出一面大镜子来,镜子里将他们各自生前结局一一映照。
富人李甲误食砒霜而死,书生贾如因夹竹桃中毒而死,商人金多多也并没有安全回乡,最终被周掌柜害死,那聚宝盆几经周折,最后也不知所踪。刘老汉归来便与老伴自缢了,距离他的六十大寿还有一个月。李文来时见到两座新坟,他磕了几个头,将银子放下便走了。而那和尚则是被王家人活活打死了,尸体便埋在寺院后的菜园中。艾草却早已疯了,黑龙族和红龙族早已湮没在历史中,只有她一人孤零零地守着蜈蚣谷,数着一个个春夏秋冬,手中永不疲倦地织着那蜈蚣锦。
镜子中的画面越闪越快,几个人却都恍然大悟,明白了自己的宿命。阎王令小鬼将几人带下去各自结案。
突然一个小鬼惊道:“阎王老爷,这里还有一个人!”
我便是这故事里的第七个人。
我叫余观鱼。
余,观,鱼。
此时,我正在看着鱼,鱼也在看着我。
如果看到这里,你还在执着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无辜的,谁罪有应得的话,那么我便很遗憾地告诉你,既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他们都只不过是路人,在各自的命途中奔波的路人。
你我也是这样。
也许你会叹息,如果李甲没有错爱,贾如和桃花没有误会,金多多的兄长没有见钱眼开,李老汉的儿子懂得变通些,小和尚把持住自己的心门,艾叶能够打开心锁,如果……
也许你会痛恨吴徵卿心狠手辣,可是有谁出生不是捧着一颗赤子之心来的,只是世事无常,在坎坷命途中,那颗心变黑了,变硬了。
吴徵卿本来也是富家子弟,从小锦衣玉食,但商场如战场,成败得失皆在转瞬之间,没有人会是永远的胜利者。
吴家很快便被竞争对手李家打败,陷入一贫如洗的境地。吴徵卿的双亲受不了打击不久便去世了,而吴徵卿无以为生,便自己卖身青楼,成了一名乐师……
我也希望,如果,我就是那个幕后黑手,在作案后洗干净双手,悠游地喝着茶,欣赏着那些被害人的惨状。然后,所有的怒气和罪责都会指向我,有人可恨,总比无人恨要好。
可是并没有如果。
我不是创造者,我只是被造物者创造的记录者。在我的眼前有一个大家看不见的鱼缸,里面有鱼儿悠然自得地游着,我触摸不到那些鱼儿,只能看着他们从鱼缸这头游向那头。
终于有一天,我决定拿起笔,将那些鱼儿一点点描绘给你看。
那些鱼儿,我只能看到它们,而只有你们才能够感受到它们。
余观鱼,汝知鱼。
本文系原创小说
本文版权由北京捧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独家所有,请勿侵权
法律顾问:天津益清(北京)律师事务所王彦玲律师
需要转载、授权、合作,请发邮件至:innearth
foxmail.转载请注明:http://www.wugonga.com/amms/4932.html